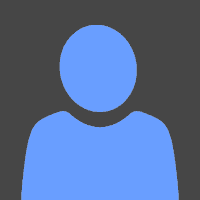安东尼·凡·戴克
Anthony van Dyck
代表作品:
艺术家名: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
生卒日期: 1599年3月22日 - 1641年12月9日
国籍:比利时
安东尼·凡·戴克的全部作品(495)
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是一位佛兰芒巴洛克艺术家,在荷兰南部和意大利获得成功后,成为英国最主要的宫廷画家。
安东尼是富裕的安特卫普丝绸商人弗兰斯·凡·戴克(Frans van Dyck)的第七个孩子,从小就作画。他在十几岁时成功地成为一名独立画家,并于1618年成为安特卫普公会的大师。此时,他正在当时北方著名画家鲁本斯的工作室工作,他对他的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1621年,凡·戴克在伦敦工作了几个月,然后回到佛兰德斯(Flanders)短暂一段时间,然后前往意大利,在那里他一直呆到1627年,主要是在热那亚。在16世纪20年代末,他完成了他备受推崇的肖像画系列,主要是其他艺术家的肖像画。从意大利回来后,他在佛兰德斯待了五年,从1630年起,他担任佛兰德斯哈布斯堡总督伊莎贝拉公爵夫人的宫廷画家。1632年,应英国查理一世的请求,他回到伦敦,成为主要宫廷画家。
除了小汉斯·霍尔拜因之外,凡·戴克和他的同时代画家委拉斯开兹是第一批主要以宫廷肖像画家的身份工作的杰出画家,彻底改变了这一流派。他最出名的是他的贵族肖像,最著名的是查理一世,他的家人和同事。在接下来的150年里,凡·戴克成为英国肖像画的主要影响者。他还画神话和圣经题材,包括祭坛画,作为一名绘图员,他表现出卓越的能力,是水彩画和蚀刻画的重要创新者。他高超的笔触,显然画得相当快,通常可以从他的许多助手所画的大面积区域中辨别出来。他的肖像风格在他工作的不同国家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最后一个英国时期的轻松优雅中达到了顶峰。他的影响延伸到现代时期。凡·戴克胡子(Van Dyke beard)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他有生之年,查理一世授予他骑士身份,他被安葬在圣保罗大教堂,这表明他在去世时的地位。
教育
安东尼·凡·戴克出生于安特卫普的富裕家庭。他的父亲是丝绸商人弗兰斯·凡·戴克(Frans van Dyck),母亲是德克·库珀斯(Dirk Cupers)和凯瑟琳·科尼克斯(Catharina Conincx)的女儿玛丽亚·库珀斯(Maria Cupers)。1599年3月23日,他接受了洗礼。他的天赋很早就显现出来,1609年他与Hendrick van Balen一起学习绘画,1615年左右成为一名独立画家,与更年轻的朋友Jan Brueghel the Younger一起建立了一个工作室。正如他的自画像1613-1614所显示的那样,在15岁时,他已经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艺术家。1618年2月,他以自由大师的身份进入安特卫普圣卢克画家协会。几年内,他将成为安特卫普和整个北欧的主要大师鲁本斯的首席助理,他充分利用了分包艺术家以及自己的大型工作室。他对这位年轻艺术家的影响是巨大的。鲁本斯称19岁的凡·戴克为“我最好的学生”。
他们关系的起源和确切性质尚不清楚。据推测,凡·戴克大约从1613年起就是鲁本斯的学生,因为即使是他的早期作品也几乎没有Hendrick van Balen风格的痕迹,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与此同时,鲁本斯在安特卫普这个相对较小且日渐衰落的城市的统治地位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凡·戴克定期返回安特卫普,但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国外度过。1620年,在鲁本斯为安特卫普耶稣会教堂(1718年失火)的天花板主要委员会签订的合同中,凡·戴克被指定为“discipelen”之一,负责按照鲁本斯的设计进行绘画。与凡·戴克不同,鲁本斯为欧洲大多数王室工作,但避免与其中任何一家王室产生排他性的联系。
意大利
1620年,在白金汉侯爵乔治·维利埃(George Villiers)的怂恿下,凡·戴克第一次前往英国,在那里为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工作,获得100英镑。正是在伦敦,在阿伦德尔伯爵的收藏中,他第一次看到了提香的作品,提香对色彩的使用和微妙的造型将证明其具有变革性,提供了一种新的风格语言,丰富了从鲁本斯那里学到的构图经验。
大约四个月后,他回到佛兰德斯,然后在1621年底离开,前往意大利,在那里呆了六年。在那里,他学习了意大利大师,同时开始了作为肖像画家的成功职业生涯。乔万·彼得罗·贝洛里(Giovan Pietro Bellori)说,他已经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重要人物,惹恼了罗马这个相当放荡不羁的北方艺术家的殖民地,带着“泽克西斯的盛况……他的行为是贵族而不是普通人,穿着华丽的衣服。由于他习惯于贵族的鲁本斯圈子,天生有高尚的思想,急于使自己脱颖而出,因此他除了穿丝绸外,还戴着一顶饰有羽毛、胸针和金链的帽子他胸前挂着一张纸条,由仆人陪同。"
他主要居住在热那亚,尽管他也到过其他城市,并在西西里岛的巴勒莫停留了一段时间,1624年瘟疫期间,他在那里被隔离,这是西西里岛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在那里,他创作了一系列重要的城市瘟疫圣罗萨利亚的绘画作品。他描绘了一位金发飘逸的年轻女子,身穿方济会斗篷,走向危险的巴勒莫市,从此成为圣徒的标准肖像画,对意大利巴洛克画家(卢卡·乔尔达诺到Pietro Novelli)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版本包括马德里、休斯顿、伦敦、纽约和巴勒莫的版本,以及波多黎各巴勒莫市的圣罗萨利亚(Saint Rosalia)和维也纳的圣罗萨利亚加冕礼。高文·亚历山大·贝利(Gauvin Alexander Bailey)和泽维尔·萨洛蒙(Xavier F.Salomon)曾研究过凡·戴克(Van Dyck)的圣罗莎莉(St Rosalia)系列绘画作品,他们都曾策划或共同策划过以意大利艺术和瘟疫为主题的展览。2020,纽约时报在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背景下,发表了一篇关于凡·戴克画圣罗莎的文章。
对于热那亚贵族来说,在最后的繁荣时期,他发展了一种全长肖像风格,借鉴了保罗·委罗内塞和提香以及鲁本斯在热那亚时期的风格,在那里,身材高大但优雅的人物以极大的傲慢俯视着观众。1627年,他回到安特卫普,在那里呆了五年,画了更多和蔼可亲的肖像,这仍然使他的佛兰芒赞助人看起来尽可能时尚。1695年,他为理事会会议厅绘制的一幅与真人大小相同的布鲁塞尔市议员集体肖像被销毁。他显然对他的赞助人很有魅力,而且,像鲁本斯一样,能够很好地融入贵族和宫廷圈子,这增加了他获得佣金的能力。到1630年,他被描述为佛兰德斯哈布斯堡总督伊莎贝拉大公爵夫人的宫廷画家。在此期间,他还创作了许多宗教作品,包括大型祭坛画,并开始了版画创作。
伦敦
查理一世国王是斯图亚特国王中最热情的艺术收藏家,他将绘画视为促进他对君主制崇高观点的一种方式。1628年,他买下了曼图亚公爵被迫出售的绝妙藏品,自1625年入主英国以来,他一直在努力将外国著名画家带到英国。1626年,他说服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在英国定居,后来他的女儿阿特米西娅·詹蒂莱斯基和一些儿子加入了他的行列。鲁本斯是一个特别的目标,他最终在1630年参加了一个外交使团,其中包括绘画,后来他从安特卫普给查尔斯寄去了更多的绘画。鲁本斯在九个月的访问期间受到了很好的待遇,在此期间他被封为爵士。查尔斯的宫廷肖像画家丹尼尔·梅滕斯(Daniel Mytens)是一个有点平庸的荷兰人。
凡·戴克与英国法庭保持联系,并帮助查尔斯国王的代理人寻找照片。他寄出了自己的一些作品,包括和查尔斯的一位经纪人恩迪米昂·波特( Endymion Porter)在一起的自画像(1623年)、他的《里纳尔多和阿米达》以及女王的宗教画像。1632年,他还在海牙为查尔斯的妹妹波希米亚王后伊丽莎白·斯图亚特(Elizabeth Stuart)作画。同年4月,凡·戴克返回伦敦,并立即被引见给国王,于7月被授予爵位,同时获得每年200英镑的养老金,国王陛下称他为普通首席画家(Principal Painter in Ordinary)。除此之外,至少在理论上,他还获得了丰厚的绘画报酬,因为查尔斯国王实际上有五年没有支付退休金,并且降低了许多绘画的价格。他在泰晤士河布莱克弗里亚(Blackfriars)有一所房子,当时就在伦敦城外。埃尔塔姆宫(Eltham Palace)的一套房间不再被皇室使用,也被作为乡村休养地供他使用。他的工作室经常受到国王和王后的参观(后来修建了一条特殊的堤道以方便他们进出),凡·戴克在世时,他们几乎没有为另一位画家坐下。
他在英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功,为国王和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以及他们的孩子画了大量肖像。许多肖像画都有好几个版本,作为外交礼物或送给日益陷入困境的国王的支持者。据估计,凡·戴克总共画了40幅查尔斯国王本人的肖像,以及大约30幅王后肖像、9幅斯特拉福德伯爵肖像和多幅其他朝臣肖像。他画了很多宫廷的画,还有他自己和他的情妇玛格丽特·莱蒙(Margaret Lemon)。
在英国,他发展了一种风格,这种风格结合了轻松的优雅和轻松,并在其主题中具有低调的权威,这种权威在18世纪末的英国肖像画中占据主导地位。许多肖像画都有一个郁郁葱葱的风景背景。他在马背上的查尔斯肖像更新了提香皇帝查尔斯五世的宏伟,但更有效、更具独创性的是他在卢浮宫拍摄的查尔斯下马画像:“查尔斯被赋予了一种本能主权的完全自然的外观,在一个故意的非正式环境中,他如此漫不经心地漫步,乍一看,他似乎是自然的绅士,而不是英国的国王。”。虽然他的肖像创造了“骑士”风格和服饰的经典理念,但事实上,他在贵族阶层中最重要的赞助人,如沃顿勋爵和贝德福德伯爵、诺森伯兰和彭布罗克,在他死后不久爆发的英国内战中都站在了议会一边。
1638年,国王枢密院通过信件专利授予凡·戴克居民身份,他与玛丽·鲁思文(Mary Ruthven)结婚,并与玛丽·鲁思文育有一个女儿。玛丽是帕特里克·鲁思文( Patrick Ruthven)的女儿,尽管头衔被取消,但他自称为鲁思文勋爵。1639-1630年间,她是一位宫廷女官(Lady-in-waiting),这桩婚姻可能是国王为了让他留在英国而鼓动的。1634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安特卫普度过,第二年又回来了。1640-1641年,随着内战的临近,他在佛兰德斯和法国度过了几个月。1640年,在波兰王子约翰·卡西米尔( John Casimir)从法国监狱获释后,他随行。
1641年8月13日,英国的罗克斯伯格夫人给海牙的一位记者的一封信报道说,凡·戴克长期患病,正在康复。11月,凡·戴克的病情恶化,他从巴黎返回英国,在那里他曾为黎塞留红衣主教作画。他于1641年12月9日在伦敦去世。在古老的圣保罗大教堂内有一座纪念他的纪念碑。
肖像和其他作品
在17世纪,肖像画的需求比其他类型的作品更强烈。凡·戴克试图说服查尔斯为白厅宴会厅委托制作关于吊袜带勋章历史的大型系列画,鲁本斯早些时候为其完成了大型天花板绘画(从安特卫普寄来)。一面墙的草图仍然存在,但到1638年,查尔斯因资金短缺而无法继续绘制。这是一个委拉斯开兹没有的问题,但同样,凡·戴克的日常生活也不像委拉斯开兹那样被琐碎的法庭职责所困扰。在他最后几年访问巴黎时,凡·戴克试图获得卢浮宫大画廊的绘画委托,但没有成功。
凡·戴克在英国创作的一系列历史画作仍然存在。它是由凡·戴克的传记作者贝洛里根据肯尼尔姆·迪格比爵士(Sir Kenelm Digby)提供的信息编写的。除了为国王所做的《丘比特与普赛克》,这些作品似乎都没有留下。但许多其他作品,更具宗教色彩而非神话色彩,确实保存了下来,尽管它们非常精美,但并没有达到委拉斯开兹历史绘画的高度。早期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鲁本斯的风格,尽管他的一些西西里作品是个人主义的。
凡·戴克的肖像画比委拉斯开兹的肖像画更讨人喜欢。 1641 年,后来的汉诺威女选举人索菲亚第一次见到流亡荷兰的亨利·埃塔·玛丽亚王后时,她写道:“凡·戴克的漂亮肖像让我对所有英国女士的美丽有了如此深刻的认识,以至于我惊讶地发现画得那么美的王后,竟是一个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小女人,皮包骨头的胳膊和牙齿从嘴里伸出来,就像防御工事一样……”
一些评论家指责凡·戴克将William Dobson、Robert Walker和Isaac Fuller等画家的新生的、更为严格的英国肖像画传统转移到了凡·戴克的许多继任者(如彼得·莱利或戈弗雷·内勒)手中,使其变得优雅而温和。传统观点总是更为有利:“当凡·戴克来到这里时,他给我们带来了面部绘画,从那时起……英格兰在这一伟大的艺术分支上超越了全世界”(乔纳森·理查森:《绘画理论论文》)。据报道,庚斯博罗在临终前曾说过:“我们都将上天堂,凡·戴克一直是这里的一员。”(We are all going to heaven, and Van Dyck is of the Company.)
在将佛兰芒水彩风景画传统引入英国的过程中,英国制作的一小部分山水水墨画或水彩画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是研究,它们在绘画背景中再现,但许多是签名和注明日期的,可能被视为作为礼物赠送的成品。其中一些细节最为详细的是黑麦港,这是一个通往欧洲大陆的港口,这表明凡·戴克在等待风力或潮汐改善的时候随意地做了这些事情。
版画
凡·戴克从意大利返回安特卫普期间,可能开始了他的肖像画创作,这成为一个非常大的版画系列,其中有同时代名人的半身肖像。他创作了绘画作品,其中18幅肖像画的头部和主要轮廓都是他自己蚀刻的,供雕刻家制作:“肖像蚀刻在他那个时代之前几乎不存在,在他的作品中,它突然出现在艺术史上达到的最高点。”。
他把大部分版画留给了专家,他们在他的画作之后雕刻。 他的蚀刻版画似乎直到他死后才出版,早期的状态非常罕见。 他的大部分印版都是在他的工作完成后印刷的。 有些在添加雕刻后以其他状态存在,有时会掩盖他的蚀刻。 他继续加入这个系列,直到至少他离开英格兰,并且大概在伦敦时加入了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
该系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是他唯一一次涉足版画。肖像画的报酬可能更高,而且他一直很受欢迎。在他去世时,有八十幅其他人的版画,其中五十二幅是艺术家的,还有他自己的十八幅。这些印版是由出版商购买的;随着这些印版在磨损后定期重新加工,它们继续印刷了几个世纪,并且该系列不断增加,到 18 世纪后期达到了 200 多幅肖像。 1851 年,这些印版被卢浮宫购买。
现在被遗忘的肖像版画系列在摄影出现之前非常受欢迎:“这个系列的重要性是巨大的,它提供了一系列图像,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被整个欧洲的肖像画家掠夺”。凡·戴克以开放线条和圆点为基础的出色蚀刻风格与该时期另一位伟大的肖像画家伦勃朗形成鲜明对比,直到 19 世纪才对艺术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肖像蚀刻的最后一个主要阶段的惠斯勒。海厄特·梅耶(Hyatt Mayor)写道:
从那时起,蚀刻师就一直在研究凡·戴克,因为他们可以希望接近他出色的直接性,而没有人希望接近伦勃朗肖像的复杂性。
工作室
凡·戴克的成功使他在伦敦维持了一个大型车间,该车间实际上成为了“肖像画生产线”。据一位来访者说,他通常只在纸上画一幅画,然后由助手放大到画布上,然后他自己画了头。客户希望绘制的服装留在工作室,通常与未完成的画布一起发送给专门绘制此类服装的艺术家。在他最后的几年里,这些工作室的合作导致了工作质量的下降。
此外,许多没有被他接触过的复制品,或者说几乎没有被他接触过的复制品,都是由工作室以及专业的复制者和后来的画家制作的。到了19世纪,伦勃朗、提香和其他画家的作品数量已大为增加。然而,他的大部分助手和文案制作人都无法接近他优雅的举止,因此与许多大师相比,艺术史学家对其归属的共识通常相对容易达成,博物馆的标签现在大多更新了(在某些情况下,乡间别墅作品的归属可能更加可疑)。
他助手中相对较少的名字是荷兰语或佛兰芒语。他可能更喜欢使用训练有素的弗莱明语,因为这一时期没有同等的英语培训。凡·戴克对英国艺术的巨大影响并不是来自通过他的学生传承下来的传统,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位有意义的英国画家来说,都不可能记录他与画室的联系。荷兰人Adriaen Hanneman1638年回到家乡海牙,成为那里的主要肖像画家。佛兰德画家彼得·蒂伊斯(Pieter Thijs)是凡·戴克最后的学生之一,在凡·戴克的工作室学习。他在家乡安特卫普成为一位非常成功的肖像和历史画家。
遗产
很久以后,他的模特们所穿的款式为凡·戴克胡须和凡·戴克衣领提供了名称,凡·戴克胡须是指他那个时代流行的尖头修剪山羊胡,凡·戴克衣领是“一种宽大的衣领,肩部有大量的花边”。乔治三世统治时期,一种被称为凡·戴克的普通“骑士”化装服很流行;盖恩斯伯勒的《蓝色男孩》穿的就是这样一套凡·戴克的服装。1774年,德比瓷器公司在约翰·佐法尼的肖像之后,刊登了一则广告,称“国王穿着范迪克礼服”。
很久以后,后人为当时男性流行的尖尖和修剪过的山羊胡起了凡·戴克胡须的名称,以及凡·戴克领,“肩部有大量蕾丝边缘的宽领”。 在乔治三世统治期间,一种名为凡·戴克的通用“骑士”化装服装很受欢迎。庚斯博罗的《蓝衣少年》穿着这样的凡·戴克服装。
1632年凡·戴克被封为爵士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英文。
纳粹掠夺的艺术品
2017年,凡·戴克(Van Dyke)的《阿德里安·亨德里克斯·莫恩斯的肖像》(Portrait of Adriaen Hendriksz Moens)被纳粹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抢走,归还给雅克·古德斯蒂克(Jacques Goudstikker)的继承人。二战后,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将这幅肖像归还荷兰,荷兰本应将其归还幸存的犹太家庭,但荷兰却将其卖给了伦敦的一位艺术品经销商,后者将其卖给了纳粹食品加工百万富翁和前纳粹党员鲁道夫·奥古斯特·奥克特( Rudolf August Oetker)。奥科特的继承人将这幅画归还给了古德斯蒂克(Jacques Goudstikker)的继承人。
生卒日期: 1599年3月22日 - 1641年12月9日
国籍:比利时
安东尼·凡·戴克的全部作品(495)
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是一位佛兰芒巴洛克艺术家,在荷兰南部和意大利获得成功后,成为英国最主要的宫廷画家。
安东尼是富裕的安特卫普丝绸商人弗兰斯·凡·戴克(Frans van Dyck)的第七个孩子,从小就作画。他在十几岁时成功地成为一名独立画家,并于1618年成为安特卫普公会的大师。此时,他正在当时北方著名画家鲁本斯的工作室工作,他对他的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1621年,凡·戴克在伦敦工作了几个月,然后回到佛兰德斯(Flanders)短暂一段时间,然后前往意大利,在那里他一直呆到1627年,主要是在热那亚。在16世纪20年代末,他完成了他备受推崇的肖像画系列,主要是其他艺术家的肖像画。从意大利回来后,他在佛兰德斯待了五年,从1630年起,他担任佛兰德斯哈布斯堡总督伊莎贝拉公爵夫人的宫廷画家。1632年,应英国查理一世的请求,他回到伦敦,成为主要宫廷画家。
除了小汉斯·霍尔拜因之外,凡·戴克和他的同时代画家委拉斯开兹是第一批主要以宫廷肖像画家的身份工作的杰出画家,彻底改变了这一流派。他最出名的是他的贵族肖像,最著名的是查理一世,他的家人和同事。在接下来的150年里,凡·戴克成为英国肖像画的主要影响者。他还画神话和圣经题材,包括祭坛画,作为一名绘图员,他表现出卓越的能力,是水彩画和蚀刻画的重要创新者。他高超的笔触,显然画得相当快,通常可以从他的许多助手所画的大面积区域中辨别出来。他的肖像风格在他工作的不同国家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最后一个英国时期的轻松优雅中达到了顶峰。他的影响延伸到现代时期。凡·戴克胡子(Van Dyke beard)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他有生之年,查理一世授予他骑士身份,他被安葬在圣保罗大教堂,这表明他在去世时的地位。
教育
安东尼·凡·戴克出生于安特卫普的富裕家庭。他的父亲是丝绸商人弗兰斯·凡·戴克(Frans van Dyck),母亲是德克·库珀斯(Dirk Cupers)和凯瑟琳·科尼克斯(Catharina Conincx)的女儿玛丽亚·库珀斯(Maria Cupers)。1599年3月23日,他接受了洗礼。他的天赋很早就显现出来,1609年他与Hendrick van Balen一起学习绘画,1615年左右成为一名独立画家,与更年轻的朋友Jan Brueghel the Younger一起建立了一个工作室。正如他的自画像1613-1614所显示的那样,在15岁时,他已经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艺术家。1618年2月,他以自由大师的身份进入安特卫普圣卢克画家协会。几年内,他将成为安特卫普和整个北欧的主要大师鲁本斯的首席助理,他充分利用了分包艺术家以及自己的大型工作室。他对这位年轻艺术家的影响是巨大的。鲁本斯称19岁的凡·戴克为“我最好的学生”。
他们关系的起源和确切性质尚不清楚。据推测,凡·戴克大约从1613年起就是鲁本斯的学生,因为即使是他的早期作品也几乎没有Hendrick van Balen风格的痕迹,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与此同时,鲁本斯在安特卫普这个相对较小且日渐衰落的城市的统治地位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凡·戴克定期返回安特卫普,但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国外度过。1620年,在鲁本斯为安特卫普耶稣会教堂(1718年失火)的天花板主要委员会签订的合同中,凡·戴克被指定为“discipelen”之一,负责按照鲁本斯的设计进行绘画。与凡·戴克不同,鲁本斯为欧洲大多数王室工作,但避免与其中任何一家王室产生排他性的联系。
意大利
1620年,在白金汉侯爵乔治·维利埃(George Villiers)的怂恿下,凡·戴克第一次前往英国,在那里为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工作,获得100英镑。正是在伦敦,在阿伦德尔伯爵的收藏中,他第一次看到了提香的作品,提香对色彩的使用和微妙的造型将证明其具有变革性,提供了一种新的风格语言,丰富了从鲁本斯那里学到的构图经验。
大约四个月后,他回到佛兰德斯,然后在1621年底离开,前往意大利,在那里呆了六年。在那里,他学习了意大利大师,同时开始了作为肖像画家的成功职业生涯。乔万·彼得罗·贝洛里(Giovan Pietro Bellori)说,他已经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重要人物,惹恼了罗马这个相当放荡不羁的北方艺术家的殖民地,带着“泽克西斯的盛况……他的行为是贵族而不是普通人,穿着华丽的衣服。由于他习惯于贵族的鲁本斯圈子,天生有高尚的思想,急于使自己脱颖而出,因此他除了穿丝绸外,还戴着一顶饰有羽毛、胸针和金链的帽子他胸前挂着一张纸条,由仆人陪同。"
他主要居住在热那亚,尽管他也到过其他城市,并在西西里岛的巴勒莫停留了一段时间,1624年瘟疫期间,他在那里被隔离,这是西西里岛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在那里,他创作了一系列重要的城市瘟疫圣罗萨利亚的绘画作品。他描绘了一位金发飘逸的年轻女子,身穿方济会斗篷,走向危险的巴勒莫市,从此成为圣徒的标准肖像画,对意大利巴洛克画家(卢卡·乔尔达诺到Pietro Novelli)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版本包括马德里、休斯顿、伦敦、纽约和巴勒莫的版本,以及波多黎各巴勒莫市的圣罗萨利亚(Saint Rosalia)和维也纳的圣罗萨利亚加冕礼。高文·亚历山大·贝利(Gauvin Alexander Bailey)和泽维尔·萨洛蒙(Xavier F.Salomon)曾研究过凡·戴克(Van Dyck)的圣罗莎莉(St Rosalia)系列绘画作品,他们都曾策划或共同策划过以意大利艺术和瘟疫为主题的展览。2020,纽约时报在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背景下,发表了一篇关于凡·戴克画圣罗莎的文章。
对于热那亚贵族来说,在最后的繁荣时期,他发展了一种全长肖像风格,借鉴了保罗·委罗内塞和提香以及鲁本斯在热那亚时期的风格,在那里,身材高大但优雅的人物以极大的傲慢俯视着观众。1627年,他回到安特卫普,在那里呆了五年,画了更多和蔼可亲的肖像,这仍然使他的佛兰芒赞助人看起来尽可能时尚。1695年,他为理事会会议厅绘制的一幅与真人大小相同的布鲁塞尔市议员集体肖像被销毁。他显然对他的赞助人很有魅力,而且,像鲁本斯一样,能够很好地融入贵族和宫廷圈子,这增加了他获得佣金的能力。到1630年,他被描述为佛兰德斯哈布斯堡总督伊莎贝拉大公爵夫人的宫廷画家。在此期间,他还创作了许多宗教作品,包括大型祭坛画,并开始了版画创作。
伦敦
查理一世国王是斯图亚特国王中最热情的艺术收藏家,他将绘画视为促进他对君主制崇高观点的一种方式。1628年,他买下了曼图亚公爵被迫出售的绝妙藏品,自1625年入主英国以来,他一直在努力将外国著名画家带到英国。1626年,他说服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在英国定居,后来他的女儿阿特米西娅·詹蒂莱斯基和一些儿子加入了他的行列。鲁本斯是一个特别的目标,他最终在1630年参加了一个外交使团,其中包括绘画,后来他从安特卫普给查尔斯寄去了更多的绘画。鲁本斯在九个月的访问期间受到了很好的待遇,在此期间他被封为爵士。查尔斯的宫廷肖像画家丹尼尔·梅滕斯(Daniel Mytens)是一个有点平庸的荷兰人。
凡·戴克与英国法庭保持联系,并帮助查尔斯国王的代理人寻找照片。他寄出了自己的一些作品,包括和查尔斯的一位经纪人恩迪米昂·波特( Endymion Porter)在一起的自画像(1623年)、他的《里纳尔多和阿米达》以及女王的宗教画像。1632年,他还在海牙为查尔斯的妹妹波希米亚王后伊丽莎白·斯图亚特(Elizabeth Stuart)作画。同年4月,凡·戴克返回伦敦,并立即被引见给国王,于7月被授予爵位,同时获得每年200英镑的养老金,国王陛下称他为普通首席画家(Principal Painter in Ordinary)。除此之外,至少在理论上,他还获得了丰厚的绘画报酬,因为查尔斯国王实际上有五年没有支付退休金,并且降低了许多绘画的价格。他在泰晤士河布莱克弗里亚(Blackfriars)有一所房子,当时就在伦敦城外。埃尔塔姆宫(Eltham Palace)的一套房间不再被皇室使用,也被作为乡村休养地供他使用。他的工作室经常受到国王和王后的参观(后来修建了一条特殊的堤道以方便他们进出),凡·戴克在世时,他们几乎没有为另一位画家坐下。
他在英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功,为国王和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以及他们的孩子画了大量肖像。许多肖像画都有好几个版本,作为外交礼物或送给日益陷入困境的国王的支持者。据估计,凡·戴克总共画了40幅查尔斯国王本人的肖像,以及大约30幅王后肖像、9幅斯特拉福德伯爵肖像和多幅其他朝臣肖像。他画了很多宫廷的画,还有他自己和他的情妇玛格丽特·莱蒙(Margaret Lemon)。
在英国,他发展了一种风格,这种风格结合了轻松的优雅和轻松,并在其主题中具有低调的权威,这种权威在18世纪末的英国肖像画中占据主导地位。许多肖像画都有一个郁郁葱葱的风景背景。他在马背上的查尔斯肖像更新了提香皇帝查尔斯五世的宏伟,但更有效、更具独创性的是他在卢浮宫拍摄的查尔斯下马画像:“查尔斯被赋予了一种本能主权的完全自然的外观,在一个故意的非正式环境中,他如此漫不经心地漫步,乍一看,他似乎是自然的绅士,而不是英国的国王。”。虽然他的肖像创造了“骑士”风格和服饰的经典理念,但事实上,他在贵族阶层中最重要的赞助人,如沃顿勋爵和贝德福德伯爵、诺森伯兰和彭布罗克,在他死后不久爆发的英国内战中都站在了议会一边。
1638年,国王枢密院通过信件专利授予凡·戴克居民身份,他与玛丽·鲁思文(Mary Ruthven)结婚,并与玛丽·鲁思文育有一个女儿。玛丽是帕特里克·鲁思文( Patrick Ruthven)的女儿,尽管头衔被取消,但他自称为鲁思文勋爵。1639-1630年间,她是一位宫廷女官(Lady-in-waiting),这桩婚姻可能是国王为了让他留在英国而鼓动的。1634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安特卫普度过,第二年又回来了。1640-1641年,随着内战的临近,他在佛兰德斯和法国度过了几个月。1640年,在波兰王子约翰·卡西米尔( John Casimir)从法国监狱获释后,他随行。
1641年8月13日,英国的罗克斯伯格夫人给海牙的一位记者的一封信报道说,凡·戴克长期患病,正在康复。11月,凡·戴克的病情恶化,他从巴黎返回英国,在那里他曾为黎塞留红衣主教作画。他于1641年12月9日在伦敦去世。在古老的圣保罗大教堂内有一座纪念他的纪念碑。
肖像和其他作品
在17世纪,肖像画的需求比其他类型的作品更强烈。凡·戴克试图说服查尔斯为白厅宴会厅委托制作关于吊袜带勋章历史的大型系列画,鲁本斯早些时候为其完成了大型天花板绘画(从安特卫普寄来)。一面墙的草图仍然存在,但到1638年,查尔斯因资金短缺而无法继续绘制。这是一个委拉斯开兹没有的问题,但同样,凡·戴克的日常生活也不像委拉斯开兹那样被琐碎的法庭职责所困扰。在他最后几年访问巴黎时,凡·戴克试图获得卢浮宫大画廊的绘画委托,但没有成功。
凡·戴克在英国创作的一系列历史画作仍然存在。它是由凡·戴克的传记作者贝洛里根据肯尼尔姆·迪格比爵士(Sir Kenelm Digby)提供的信息编写的。除了为国王所做的《丘比特与普赛克》,这些作品似乎都没有留下。但许多其他作品,更具宗教色彩而非神话色彩,确实保存了下来,尽管它们非常精美,但并没有达到委拉斯开兹历史绘画的高度。早期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鲁本斯的风格,尽管他的一些西西里作品是个人主义的。
凡·戴克的肖像画比委拉斯开兹的肖像画更讨人喜欢。 1641 年,后来的汉诺威女选举人索菲亚第一次见到流亡荷兰的亨利·埃塔·玛丽亚王后时,她写道:“凡·戴克的漂亮肖像让我对所有英国女士的美丽有了如此深刻的认识,以至于我惊讶地发现画得那么美的王后,竟是一个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小女人,皮包骨头的胳膊和牙齿从嘴里伸出来,就像防御工事一样……”
一些评论家指责凡·戴克将William Dobson、Robert Walker和Isaac Fuller等画家的新生的、更为严格的英国肖像画传统转移到了凡·戴克的许多继任者(如彼得·莱利或戈弗雷·内勒)手中,使其变得优雅而温和。传统观点总是更为有利:“当凡·戴克来到这里时,他给我们带来了面部绘画,从那时起……英格兰在这一伟大的艺术分支上超越了全世界”(乔纳森·理查森:《绘画理论论文》)。据报道,庚斯博罗在临终前曾说过:“我们都将上天堂,凡·戴克一直是这里的一员。”(We are all going to heaven, and Van Dyck is of the Company.)
在将佛兰芒水彩风景画传统引入英国的过程中,英国制作的一小部分山水水墨画或水彩画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是研究,它们在绘画背景中再现,但许多是签名和注明日期的,可能被视为作为礼物赠送的成品。其中一些细节最为详细的是黑麦港,这是一个通往欧洲大陆的港口,这表明凡·戴克在等待风力或潮汐改善的时候随意地做了这些事情。
版画
凡·戴克从意大利返回安特卫普期间,可能开始了他的肖像画创作,这成为一个非常大的版画系列,其中有同时代名人的半身肖像。他创作了绘画作品,其中18幅肖像画的头部和主要轮廓都是他自己蚀刻的,供雕刻家制作:“肖像蚀刻在他那个时代之前几乎不存在,在他的作品中,它突然出现在艺术史上达到的最高点。”。
他把大部分版画留给了专家,他们在他的画作之后雕刻。 他的蚀刻版画似乎直到他死后才出版,早期的状态非常罕见。 他的大部分印版都是在他的工作完成后印刷的。 有些在添加雕刻后以其他状态存在,有时会掩盖他的蚀刻。 他继续加入这个系列,直到至少他离开英格兰,并且大概在伦敦时加入了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
该系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是他唯一一次涉足版画。肖像画的报酬可能更高,而且他一直很受欢迎。在他去世时,有八十幅其他人的版画,其中五十二幅是艺术家的,还有他自己的十八幅。这些印版是由出版商购买的;随着这些印版在磨损后定期重新加工,它们继续印刷了几个世纪,并且该系列不断增加,到 18 世纪后期达到了 200 多幅肖像。 1851 年,这些印版被卢浮宫购买。
现在被遗忘的肖像版画系列在摄影出现之前非常受欢迎:“这个系列的重要性是巨大的,它提供了一系列图像,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被整个欧洲的肖像画家掠夺”。凡·戴克以开放线条和圆点为基础的出色蚀刻风格与该时期另一位伟大的肖像画家伦勃朗形成鲜明对比,直到 19 世纪才对艺术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肖像蚀刻的最后一个主要阶段的惠斯勒。海厄特·梅耶(Hyatt Mayor)写道:
从那时起,蚀刻师就一直在研究凡·戴克,因为他们可以希望接近他出色的直接性,而没有人希望接近伦勃朗肖像的复杂性。
工作室
凡·戴克的成功使他在伦敦维持了一个大型车间,该车间实际上成为了“肖像画生产线”。据一位来访者说,他通常只在纸上画一幅画,然后由助手放大到画布上,然后他自己画了头。客户希望绘制的服装留在工作室,通常与未完成的画布一起发送给专门绘制此类服装的艺术家。在他最后的几年里,这些工作室的合作导致了工作质量的下降。
此外,许多没有被他接触过的复制品,或者说几乎没有被他接触过的复制品,都是由工作室以及专业的复制者和后来的画家制作的。到了19世纪,伦勃朗、提香和其他画家的作品数量已大为增加。然而,他的大部分助手和文案制作人都无法接近他优雅的举止,因此与许多大师相比,艺术史学家对其归属的共识通常相对容易达成,博物馆的标签现在大多更新了(在某些情况下,乡间别墅作品的归属可能更加可疑)。
他助手中相对较少的名字是荷兰语或佛兰芒语。他可能更喜欢使用训练有素的弗莱明语,因为这一时期没有同等的英语培训。凡·戴克对英国艺术的巨大影响并不是来自通过他的学生传承下来的传统,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位有意义的英国画家来说,都不可能记录他与画室的联系。荷兰人Adriaen Hanneman1638年回到家乡海牙,成为那里的主要肖像画家。佛兰德画家彼得·蒂伊斯(Pieter Thijs)是凡·戴克最后的学生之一,在凡·戴克的工作室学习。他在家乡安特卫普成为一位非常成功的肖像和历史画家。
遗产
很久以后,他的模特们所穿的款式为凡·戴克胡须和凡·戴克衣领提供了名称,凡·戴克胡须是指他那个时代流行的尖头修剪山羊胡,凡·戴克衣领是“一种宽大的衣领,肩部有大量的花边”。乔治三世统治时期,一种被称为凡·戴克的普通“骑士”化装服很流行;盖恩斯伯勒的《蓝色男孩》穿的就是这样一套凡·戴克的服装。1774年,德比瓷器公司在约翰·佐法尼的肖像之后,刊登了一则广告,称“国王穿着范迪克礼服”。
很久以后,后人为当时男性流行的尖尖和修剪过的山羊胡起了凡·戴克胡须的名称,以及凡·戴克领,“肩部有大量蕾丝边缘的宽领”。 在乔治三世统治期间,一种名为凡·戴克的通用“骑士”化装服装很受欢迎。庚斯博罗的《蓝衣少年》穿着这样的凡·戴克服装。
1632年凡·戴克被封为爵士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英文。
纳粹掠夺的艺术品
2017年,凡·戴克(Van Dyke)的《阿德里安·亨德里克斯·莫恩斯的肖像》(Portrait of Adriaen Hendriksz Moens)被纳粹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抢走,归还给雅克·古德斯蒂克(Jacques Goudstikker)的继承人。二战后,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将这幅肖像归还荷兰,荷兰本应将其归还幸存的犹太家庭,但荷兰却将其卖给了伦敦的一位艺术品经销商,后者将其卖给了纳粹食品加工百万富翁和前纳粹党员鲁道夫·奥古斯特·奥克特( Rudolf August Oetker)。奥科特的继承人将这幅画归还给了古德斯蒂克(Jacques Goudstikker)的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