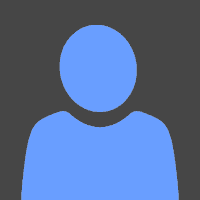保罗·高更
Paul Gauguin
代表作品:
艺术家名:保罗·高更(Paul Gauguin)
生卒日期: 1848年6月7日 - 1903年5月8日
国籍:法国
保罗·高更的全部作品(611)
欧仁·亨利·保罗·高更(Eugène Henri Paul Gauguin)是法国后印象派艺术家。直到他死后才被人欣赏,高更现在因其对色彩和与印象派不同的合成风格的实验性使用而受到认可。在他生命的尽头,他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度过了十年。这个时期的绘画描绘了那个地区的人物或风景。
他的作品影响了法国前卫和许多现代艺术家,如毕加索和亨利·马蒂斯,他以与文森特·梵高和西奥·梵高的关系而闻名。高更的艺术在他去世后开始流行,部分原因是经销商安布罗斯·沃拉德 (Ambroise Vollard) 的努力,他在职业生涯后期组织了他的作品展览,并协助在巴黎组织了两次重要的死后展览。
作为画家、雕塑家、版画家、陶艺家和作家,高更是象征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在景泰蓝风格的影响下,在绘画中表达题材的内在意义,为原始主义和回归田园主义铺平了道路。他也是木雕和木刻作为艺术形式的有影响力的支持者。
家族史和早年生活
高更于 1848 年 6 月 7 日出生在巴黎,其父母为克洛维斯·高更 (Clovis Gauguin) 和艾琳·查扎尔 (Aline Chazal)。他的出生恰逢同年整个欧洲的革命动荡。他的父亲是一名 34 岁的自由派记者,来自居住在奥尔良的一个企业家家庭。当他为之撰写的报纸被法国当局压制时,他被迫逃离法国。高更的母亲是雕刻家安德烈·查扎尔 (André Chazal) 和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作家和活动家弗洛拉·特里斯坦 (Flora Tristan) 的女儿。当安德烈袭击他的妻子弗洛拉并因谋杀未遂被判入狱时,他们的结合结束了。
保罗·高更的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 Flora Tristan)是泰蕾莎·莱斯奈( Thérèse Laisnay)和唐·马里亚诺·德·特里斯坦·莫斯科索(Don Mariano de Tristan Moscoso)的私生女。 泰蕾莎(Thérèse)的详细家庭背景不得而知,唐·马里亚诺 (Don Mariano) 来自秘鲁阿雷基帕市的一个西班牙贵族家庭。他是龙骑兵的一名军官。富有的特里斯坦莫斯科索家族的成员在秘鲁担任重要职位。尽管如此,唐马里亚诺的意外死亡使他的情妇和女儿弗洛拉陷入贫困。当弗洛拉与安德烈的婚姻失败时,她向她父亲的秘鲁亲戚请愿并获得了一笔小额赔偿金。她航行到秘鲁,希望扩大她在特里斯坦莫斯科索家族财富中的份额。这从未实现,但她成功地出版了一本关于她在秘鲁的经历的流行游记,并于 1838 年开启了她的文学生涯。作为早期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支持者,高更的外祖母为 1848 年的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 1844 年,她被法国警察监视并因过度劳累而去世。她的孙子保罗“崇拜他的祖母,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随身携带她的书”。
1850 年,克洛维斯·高更 (Clovis Gauguin) 带着妻子艾琳 (Aline) 和年幼的孩子前往秘鲁,希望在妻子南美关系的支持下继续他的新闻事业。他在途中死于心脏病,艾琳作为寡妇与 18 个月大的保罗和他的2岁半的姐姐玛丽一起抵达秘鲁。高更的母亲受到她祖父的欢迎,他的女婿不久将担任秘鲁总统。到六岁时,保罗享受着特权的成长,有保姆和仆人陪伴。他保留了童年时期的生动记忆,这给他灌输了“无法磨灭的秘鲁印象,困扰着他的余生”。
1854 年秘鲁内战期间,当他的家庭支柱跟随政治权力机构倒台时,高更田园诗般的童年戛然而止。艾琳带着她的孩子返回法国,将保罗与他的祖父纪尧姆·高更留在奥尔良。秘鲁特里斯坦莫斯科索家族剥夺了她的外祖父安排的丰厚年金,艾琳在巴黎定居,担任裁缝。
教育和第一份工作
在参加了当地的几所学校后,高更被送到了著名的天主教寄宿学校拉夏贝尔圣梅斯敏小修院。他在学校待了三年。 14 岁时,他进入巴黎的洛里奥尔学院(Loriol Institute),这是一所海军预备学校,然后返回奥尔良,在圣女贞德中学度过他的最后一年。高更签约成为商船的驾驶员助理。三年后,他加入法国海军,服役两年。他的母亲于 1867 年 7 月 7 日去世,但几个月后他才知道这件事,直到他姐姐玛丽的一封信赶上了在印度的高更。
1871 年,高更回到巴黎,在那里找到了一份股票经纪人的工作。一位亲密的家庭朋友古斯塔夫·阿罗萨 (Gustave Arosa) 让他在巴黎证券交易所找到了一份工作;高更 23 岁。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巴黎商人,并在接下来的 11 年里一直保持着这一地位。 1879 年,他作为一名股票经纪人每年赚取 30,000 法郎(按 2019 年美元计算约为 145,000 美元),在他在艺术市场的交易中再次获得同样的收入。但在 1882 年,巴黎股市崩盘,艺术品市场萎缩。高更的收入急剧下降,他最终决定全职从事绘画。
婚姻
1873 年,他与丹麦妇女 梅特-索菲·盖德(Mette-Sophie Gad,1850–1920) 结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们有五个孩子:埃米尔(Émile,1874-1955)、艾琳 (Aline,1877–1897)、克洛维斯 (Clovis,1879–1900)、让·勒内 ( Jean René,1881–1961)、和保罗·罗伦 ( Paul Rollon,1883–1961)。到 1884 年,高更与家人搬到丹麦哥本哈根,在那里他从事防水布推销员的商业生涯。这并不成功:他不会说丹麦语,而且丹麦人不想要法国防水油布。梅特成为主要的养家糊口的人,为见习外交官提供法语课程。
当高更被迫从事全职绘画工作 11 年后,他的中产阶级家庭和婚姻破裂了。 1885 年,在他的妻子和她的家人要求他离开之后,他回到了巴黎,因为他已经放弃了他们共同的价值观。高更与他们最后一次身体接触是在 1891 年,梅特最终在 1894 年果断地与他决裂。
第一幅画
1873 年,大约在他成为股票经纪人的同时,高更开始在空闲时间画画。他的巴黎生活以巴黎第九区为中心。高更住在 布鲁耶尔街(rue la Bruyère)15号。附近是印象派画家经常光顾的咖啡馆。高更还经常参观画廊并购买新兴艺术家的作品。他与毕沙罗 建立了友谊,并在星期天拜访他,在他的花园里作画。毕沙罗向他介绍了其他各种艺术家。 1877 年,高更“搬到了低端市场,穿过河流,搬到了更贫穷、更新的城市蔓延”沃吉拉尔。在这里三楼,他有第一个拥有工作室的家。
他的密友埃米尔·舒芬尼克住在附近,他曾是一名股票经纪人,也渴望成为一名艺术家。高更在 1881 年和 1882 年举办的印象派展览中展示了绘画。他的画作受到了不屑一顾的评价,尽管其中一些,例如《沃吉拉德的市场花园》,现在受到高度评价。
1882 年,股市崩盘,艺术品市场萎缩。印象派的主要艺术品经销商保罗·杜兰德-鲁埃尔 (Paul Durand-Ruel) 受崩盘的影响尤其严重,并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从高更等画家那里购买画作。高更的收入急剧下降,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慢慢制定了成为全职艺术家的计划。接下来的两个夏天,他与毕沙罗一起画画,偶尔也与保罗·塞尚一起画画。
1883 年 10 月,他写信给毕沙罗,说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以绘画为生,并寻求他的帮助,而毕沙罗起初欣然提供了帮助。次年一月,高更与家人搬到鲁昂,在那里他们可以住得更便宜,而且他认为他在去年夏天访问毕沙罗时发现了机会。然而,这次冒险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到年底,梅特和孩子们搬到了哥本哈根,之后不久于 1884 年 11 月,高更带着他的艺术收藏品,随后留在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的生活同样艰难,他们的婚姻也变得紧张起来。在梅特的敦促和家人的支持下,高更于次年返回巴黎。
法国 1885–1886
1885 年 6 月,高更在他 6 岁的儿子克洛维斯的陪同下返回巴黎。其他孩子留在哥本哈根的梅特身边,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家人和朋友的支持,而梅特本人则能够找到翻译和法语教师的工作。高更最初发现很难重新进入巴黎的艺术界,并在真正的贫困中度过了他的第一个冬天,不得不从事一系列卑微的工作。克洛维斯最终病倒并被送到寄宿学校,高更的姐姐玛丽提供了资金。在第一年,高更创作的艺术作品很少。 1886 年 5 月,他在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印象派展览上展出了 19 幅画作和一幅木浮雕。
这些画作大多是鲁昂或哥本哈根的早期作品,尽管他的《女人洗澡》引入了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即海浪中的女人,但在少数新作品中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新奇。尽管如此,Félix Bracquemond确实购买了他的一幅画。此次展览还确立了乔治·修拉作为巴黎前卫运动的领导者的地位。高更轻蔑地拒绝了修拉的新印象派点彩画技巧,并在今年晚些时候果断地与毕沙罗决裂,从那时起,毕沙罗对高更颇为敌视。
1886 年夏天,高更在布列塔尼的阿文桥艺术家殖民地度过。他之所以被吸引,首先是因为住在那里很便宜。然而,他发现自己在夏天涌入那里的年轻艺术学生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天生好斗的气质(他既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拳击手又是击剑手)在社交轻松的海滨度假胜地没有任何障碍。在那个时期,他的古怪外表和他的艺术都被人们铭记。在这些新同事中,Charles Laval将在次年陪同高更前往巴拿马和马提尼克岛。
那年夏天,他以毕沙罗(Pissarro)和德加(Degas)在 1886 年第八届印象派展览上展出的方式绘制了一些裸体人物的粉彩画。他主要画风景如《布雷顿牧羊女》,其中人物扮演次要角色。他的《布列塔尼男孩洗澡》介绍了他每次访问阿文桥时都会回到的主题,显然要感谢埃德加·德加的设计和对纯色的大胆使用。英国插画家Randolph Caldecott的天真画作曾用于描绘一本关于布列塔尼的流行指南,吸引了阿文桥 (Pont-Aven) 前卫学生艺术家的想象力,他们渴望摆脱学院派的保守主义,而高更 (Gauguin)有意识地在他的布列塔尼女孩素描中模仿它们。这些草图后来在他的巴黎工作室被加工成画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四个布雷顿女人》,它与他早期的印象派风格明显不同,并融入了凯迪克插图的天真品质,将特征夸大到了漫画的地步。
高更与埃米尔·伯纳德、Charles Laval、埃米尔·舒芬尼克和其他许多人在巴拿马和马提尼克岛旅行后重新访问了阿文桥。纯色的大胆使用和象征主义题材的选择区分了现在所谓的阿文桥派( Pont-Aven School)。对印象派失望的高更觉得欧洲传统绘画过于模仿,缺乏象征深度。相比之下,非洲和亚洲的艺术在他看来充满了神秘的象征意义和活力。当时欧洲流行其他文化的艺术,尤其是日本(日本主义)的艺术。 1889年应邀参加二十(Les XX)组织的展览。
分割主义(Cloisonnism,又名景泰蓝主义)和综合主义( synthetism,又名合成主义)
在民间艺术和日本版画的影响下,高更的作品向分割主义方向发展,这种风格由评论家爱德华·杜雅尔丹(Édouard Dujardin)命名,用来描述埃米尔·伯纳德(Émile Bernard)的色彩平坦区域和大胆轮廓的绘画方法,使杜雅尔丹想起中世纪的景泰蓝珐琅技术。高更非常欣赏伯纳德的艺术以及他大胆采用适合高更的风格来表达他的艺术作品的本质。
在高更的《黄色的基督》中,这幅画经常被引用为景泰蓝主义的典型作品,图像被简化为由浓黑轮廓分隔的纯色区域。在这样的作品中,高更很少注意古典透视,大胆地消除了微妙的色彩层次,从而摒弃了文艺复兴后绘画的两个最典型的原则。他的绘画后来演变为合成主义,其中形式和色彩均不占主导地位,但两者均具有同等作用。
马提尼克
1887 年,在访问了巴拿马之后,高更于 6 月至 11 月在加勒比海马提尼克岛的圣皮埃尔( Saint Pierre)附近度过,并由他的朋友艺术家Charles Laval陪同。他在这段时间的想法和经历都记录在他给妻子梅特(Mette)和他的艺术家朋友埃米尔·舒芬尼克的信中。他通过巴拿马到达马提尼克岛,在那里他发现自己破产了,没有工作。当时法国有一项遣返政策,如果公民破产或滞留在法国殖民地,国家将支付回程费用。离开巴拿马后,在遣返政策的保护下,高更和拉瓦尔决定在马提尼克岛的圣皮埃尔港下船。对于高更是有意还是自发决定留在岛上,学者们意见不一。
起初,他们住的“黑人小屋”很适合他,他喜欢观察人们的日常活动。然而,夏天的天气很热和小屋在雨中漏水了。高更还患上了痢疾和沼泽热。在马提尼克岛期间,他创作了 10 到 20 部作品(最常见的估计是 12 部),广泛旅行,显然与一小群印度移民接触过,这种接触后来通过融入印度符号影响了他的艺术。在他逗留期间,作家拉夫卡迪奥·赫恩( Lafcadio Hearn)也在岛上。他的叙述提供了一个历史比较以配合高更的图像。
高更在马提尼克岛逗留期间完成了 11 幅著名的画作,其中许多似乎来自他的小屋。他写给埃米尔·舒芬尼克的信表达了对他画作中所代表的异国情调和当地人的兴奋。高更断言,他在岛上的四幅画作比其他画作更好。作品整体色彩鲜艳,画松散,户外人物场景。虽然他在岛上的时间很短,但肯定是有影响的。他在后来的画作中回收了他的一些人物和草图,例如在他的粉丝身上复制的芒果中的主题。高更离开该岛后,农村和土著居民仍然是高更作品中的热门主题。
文森特和提奥·梵高
高更的马提尼克岛画作在他的颜料商人阿尔塞纳·普瓦捷(Arsène Poitier) 的画廊展出。在那里,文森特·梵高和他的艺术品经销商兄弟提奥看到并钦佩他们。西奥以 900 法郎的价格购买了高更的三幅画,并安排将它们挂在古皮家,从而将高更介绍给了富有的客户。在 1891 年提奥去世后,古比尔的这种安排仍在继续。同时,文森特和高更成为了亲密的朋友,他们一起在艺术上通信,这种通信有助于高更制定他的艺术哲学。
1888 年,在提奥的怂恿下,高更和文森特在法国南部阿尔勒的文森特黄屋共画了九周。高更与文森特的关系令人担忧。他们的关系恶化,最终高更决定离开。 1888 年 12 月 23 日晚上,根据后来对高更的描述,文森特用一把直剃刀对着高更。当天晚上晚些时候,他割掉了自己的左耳。他用报纸把切下的耳朵包起来,送给在高更和文森特都去过的妓院工作的一位女士,并要求她“小心保管这件物品,以纪念我”。第二天文森特住院,高更离开了阿尔勒。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继续通信,1890 年,高更甚至提议他们在安特卫普成立一个艺术家工作室。 1889 年的雕塑自画像《头形壶》(Jug in the Form of a Head )似乎参考了高更与文森特的创伤关系。
高更后来声称在影响文森特·梵高作为阿尔勒画家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文森特在《埃顿花园的记忆》等画作中对高更的“从想象中绘画”的理论进行了简短的实验,但这并不适合他,他很快又回到了从自然中绘画。
埃德加·德加
尽管高更在毕沙罗的领导下在艺术界取得了一些早期的进步,但埃德加·德加是高更最受尊敬的当代艺术家,从一开始就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人物和室内设计以及歌手的雕刻和彩绘奖章瓦莱丽·鲁米。他对德加的艺术尊严和机智深怀敬意。这是高更最健康、最持久的友谊,贯穿了他的整个艺术生涯,直到他去世。
德加成为他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亲自购买高更的作品并说服经销商保罗·杜兰德-鲁埃尔也这样做,没有谁比德加更坚定地公开支持高更了。高更还在 1870 年代早期到中期从德加那里购买了作品,他自己的单一类型倾向可能受到德加在媒介方面的进步的影响。
1893 年 11 月,德加主要组织的高更的杜朗-鲁埃尔(Durand-Ruel)展览收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嘲笑者包括克劳德·莫奈、雷诺阿和前朋友毕沙罗。然而,德加称赞了他的作品,购买了《我停下》并欣赏高更变幻出的民间传说的异国奢华。作为欣赏,高更向德加赠送了《月亮和地球》,这是曾引起最敌对批评的展出画作之一。高更的油画《沙滩上的骑手》(两个版本)回忆德加在 1860 年代开始的马匹主题绘画,特别是《赛前》,证明了他对高更的持久影响。德加后来在高更 1895 年的拍卖会上购买了两幅画作,为他最后一次去塔希提岛的旅行筹集资金。这些是 《女人和芒果》和高更画的爱德华·马奈的《奥林匹亚》版本。
第一次去大溪地
到 1890 年,高更构思了将大溪地作为下一个艺术目的地的计划。 1891 年 2 月在巴黎德鲁奥酒店成功拍卖画作,以及宴会和慈善音乐会等其他活动,提供了必要的资金。高更通过毕沙罗向奥克塔夫·米尔博 (Octave Mirbeau) 发表了讨人喜欢的评论,这极大地帮助了拍卖。在哥本哈根探望妻儿后,高更于 1891 年 4 月 1 日启航前往塔希提岛,并承诺返回一个富人并重新开始,这是最后一次。他公开的意图是逃避欧洲文明和“一切人为和传统的东西”。尽管如此,他还是小心翼翼地随身携带了一系列图画、素描和印刷品形式的视觉刺激。
他在殖民地首都帕皮提( Papeete)度过了前三个月,已经深受法国和欧洲文化的影响。他的传记作者贝琳达·汤姆森 (Belinda Thomson) 观察到,他对原始田园诗的想象一定很失望。他无法负担在帕皮提追求享乐的生活方式,早期的肖像画《苏珊班布里奇肖像》并不受欢迎。他决定在距离帕皮提约 45 公里(28 英里)的帕皮阿里马泰亚建立他的工作室,将自己安置在一个本土风格的竹屋里。在这里,他创作了描绘大溪地生活的画作,如《海边》和 《冰冷的玛丽亚》,后者成为他最珍贵的大溪地画作。
他的许多最优秀的画作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他的第一个大溪地模特肖像被认为是 《拿着花的大溪地女人》。这幅画以其描绘波利尼西亚特征的谨慎而著称。他把这幅画寄给了他的赞助人乔治·丹尼尔·德·蒙弗莱德( George-Daniel de Monfreid),他是埃米尔·舒芬尼克的朋友,后者将成为高更在大溪地的忠实拥护者。到 1892 年夏末,这幅画在巴黎古皮尔画廊展出。艺术史学家南希·莫尔·马修斯(Nancy Mowll Mathews)认为,高更在大溪地遇到的异国情调,在这幅画中如此明显,是他在那里逗留的最重要的方面。
高更借了雅克-安托万·莫伦豪特 (Jacques-Antoine Moerenhout) 1837 年的《去大洋群岛旅行》(Voyage aux îles du Grand Océan)和埃德蒙·德博维斯 (Edmond de Bovis) 的 1855 年的《欧洲人到来时的塔希提社会状况》( État de la société tahitienne à l'arrivée des Européens),其中包含对大溪地被遗忘的宗教的完整描述。高更对波利尼西亚社会 (Arioi )和他们的神奥罗(Ora)的叙述着迷。因为这些记载没有插图,而且大溪地的模型反正早就消失了,他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创作了大约二十幅画作和十多幅木雕。其中第一个是《舞蹈种子》,代表奥罗(Oro)在陆地的妻子 瓦劳马蒂(Vairaumati),现在由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他当时的插图笔记本 《古代的崇拜马霍里》(Ancien Culte Mahorie )保存在卢浮宫,并于 1951 年以影印形式出版。
高更总共将他的九幅画寄给了巴黎的蒙弗莱德(Monfreid)。这些作品最终在哥本哈根与已故文森特·梵高的联合展览中展出。他们受到好评的报道(尽管实际上只有两幅大溪地画作售出,而且他早期的画作与梵高的画作相比并不有利)足以鼓舞高更考虑带着他完成的其他七十幅画回来。在任何情况下,他的资金基本上都用完了,这取决于国家对免费回家的补助。此外,他还有一些健康问题,当地医生诊断为心脏问题,马修斯认为这可能是心血管梅毒的早期迹象。
高更后来写了一篇名为《诺阿诺阿》(Noa Noa,1901 年首次出版) 的游记,最初被认为是对他的画作的评论,并描述了他在大溪地的经历。现代评论家认为这本书的内容部分是幻想和抄袭。他在其中透露,此时他娶了一个 13 岁的女孩为本地妻子(vahine,大溪地语中的“女人”),婚姻在一个下午的过程中缔结。这就是特哈阿马纳(Teha'amana) ,在游记中被称为特胡拉(Tehura),她在 1892 年夏末怀孕。 特哈阿马纳是高更几幅画作的主题,包括 《马拉希梅图亚不提哈马纳》和著名的《游魂》,以及现在在奥赛博物馆中的著名木雕《特胡拉》( Tehura)。到 1893 年 7 月末,高更他决定离开塔希提岛,即使几年后返回该岛,他也永远不会再见到特哈阿马纳或她的孩子。
返回法国
1893 年 8 月,高更回到法国,继续创作大溪地题材的画作,如 《神之日》和《神圣的春天,甜蜜的梦》。 1894 年 11 月在杜兰鲁尔画廊举办的展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展出的 40 幅画作中有 11 幅以相当高的价格出售。他在艺术家经常光顾的蒙帕纳斯区边缘的维辛埃托里克斯街(rue Vercingétorix)6号 设立了一套公寓,并开始每周举办一次沙龙。他扮演了一个异国情调的角色,穿着波利尼西亚人的服装,并与一名仍处于十几岁的年轻女子,“半印度半马来亚人”,被称为爪哇人安娜的公开恋情。
尽管他 11 月的展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他随后在不明朗的情况下失去了杜兰·鲁尔(Durand-Ruel )的赞助。马修斯将此描述为高更职业生涯的悲剧。除其他外,他失去了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 1894 年初,他发现他使用实验技术为他提议的游记《诺阿诺阿》(Noa Noa) 准备木刻版画。他在夏天回到了蓬艾文。 1895 年 2 月,他试图在巴黎的德鲁奥酒店(Hôtel Drouot)拍卖他的画作,类似于 1891 年的那幅画,但没有成功。然而,1895 年 3 月,经销商安布罗斯·沃拉德(Ambroise Vollard) 在他的画廊展示了他的画作,但不幸的是,他们当时并没有达成协议。
他向 1895 年 4 月开幕的法国国立美术学院(Société Nationale des Beaux-Arts) 沙龙提交了一件他称之为《野生》(Oviri,大溪地神话中是哀悼女神) 的大型陶瓷雕塑,这是他去年冬天烧制的。关于它的接受方式有不同的版本:他的传记作者和《诺阿诺阿》的合作者,象征主义诗人查尔斯·莫里斯( Charles Morice),争辩说(1920 年)这幅作品被“从字面上驱逐”了展览。无论如何,高更借此机会向晚报写了一封关于现代陶瓷状况的愤怒信,以增加他的公众曝光率。
到这个时候,他和他的妻子梅特已经不可挽回地分居了。虽然有和解的希望,但他们很快就因金钱问题吵架,谁也没有去拜访对方。高更最初拒绝分享他的叔叔伊西多尔 (Isidore) 的 13,000 法郎遗产中的任何部分,这是他回国后不久获得的。梅特最终得到了 1,500 法郎的礼物,但她很生气,从那时起就只通过埃米尔·舒芬尼克与他保持联系——这对高更来说是双重的痛苦,因为他的朋友因此知道他背叛的真实程度。
到 1895 年中期,为高更返回塔希提岛筹集资金的尝试失败了,他开始接受朋友的慈善事业。 1895 年 6 月,尤金·卡里埃 安排了一条廉价通道返回大溪地,高更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欧洲。
住在大溪地
高更于 1895 年 6 月 28 日再次启程前往塔希提岛。这次回归本质上是负面的,他对巴黎艺术界的幻想破灭,在同一期《风雅信使》(Mercure de France)上两次攻击他,一个是埃米尔·伯纳德,另一个是卡米尔·莫克莱尔( Camille Mauclair)的。马修斯评论说,他在巴黎的孤立变得如此痛苦,以至于他别无选择,只能试图重新获得他在大溪地社会中的地位。
他于 1895 年 9 月抵达,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帕皮提附近或有时在帕皮提附近过着看似舒适的艺术家殖民地生活。在此期间,他能够通过越来越稳定的销售流以及朋友和祝福者的支持来养活自己,尽管在 1898 年至 1899 年的一段时间里,他感到不得不在帕皮提从事办公桌工作,其中没有多少记录。他在帕皮提以东十英里的富裕地区普纳奥亚建造了一座宽敞的芦苇和茅草屋,由富裕家庭定居,他在其中安装了一个大工作室,不惜一切代价。朱尔斯·阿戈斯蒂尼(Jules Agostini)是高更的熟人,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业余摄影师,于 1896 年拍摄了这所房子。后来土地出售迫使他在同一个街区建造了一座新房子。
他养了一匹马和马车,因此可以每天前往帕皮提,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参加殖民地的社交生活。他订阅《风雅信使》(Mercure de France),是当时法国最重要的评论期刊,并与巴黎的艺术家、经销商、评论家和赞助人保持着积极的通信。在帕皮提的那一年及此后,他在当地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最近成立的反对殖民政府的当地期刊 《黄蜂》(Les Guêpes,The Wasps)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最终成为月刊的编辑。他的报纸上有一定数量的艺术品和木刻版画幸存下来。 1900 年 2 月,他成为《黄蜂》 的编辑,并为此领取薪水,并继续担任编辑,直到 1901 年 9 月离开塔希提岛。 但实际上并不是本土事业的拥护者,尽管有些人们如此认为。
至少在第一年,他没有创作任何画作,这告诉蒙弗雷德,他打算从此专注于雕塑。他这一时期的木雕很少能幸存下来,其中大部分是蒙弗雷德收集的。当他恢复绘画时,继续他长期存在的一系列充满性感的裸体画作,如《上帝之子》和《永远》。汤姆森观察到复杂性的进展。马修斯注意到基督教象征主义的回归,这会让他受到当时殖民者的喜爱,现在急于通过强调宗教原则的普遍性来保护本土文化的剩余部分。在这些画作中,高更正在解决他的听众是他在帕皮提的殖民者同胞,而不是他以前在巴黎的前卫听众。
他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他因各种疾病多次住院。当他在法国时,他在去孔卡尔诺的海边旅行中因醉酒斗殴而摔断了脚踝。伤口,开放性骨折,从未正确愈合。然后限制他行动的痛苦和虚弱的疮开始在他的腿上上下爆发。这些用砷处理。高更指责热带气候并将疮描述为“湿疹”,但他的传记作者同意这一定是梅毒的进展。
1897 年 4 月,他收到消息,他最喜欢的女儿艾琳死于肺炎。这也是他得知他不得不腾出房子的月份,因为它的土地已经卖掉了。他向银行贷款,建造了一座更加奢华的木屋,享有山景和海景。但他这样做太过分了,到年底时他面临着银行对他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真实前景。健康状况不佳和债务紧迫,使他濒临绝望。年底,他完成了他不朽的作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他认为这是他的杰作和最后的艺术遗嘱,在给乔治·丹尼尔·蒙弗里德的一封信中,他解释说他在完成后试图自杀。这幅画于次年 11 月与他在 7 月之前完成的八幅主题相关的画作一起在沃拉德(Vollard)的画廊展出。这是他自 1893 年杜朗-鲁埃尔展览以来的第一次在巴黎举办的大型展览,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评论家称赞他的新宁静。然而,作品收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沃拉德很难将其出售。他最终在 1901 年以 2,500 法郎(2000 年美元约 10,000 美元)的价格将其卖给了 加布里埃尔·弗里索(Gabriel Frizeau),其中沃拉德的佣金可能高达 500 法郎。
1899 年秋天,高更的巴黎经销商乔治·肖德(Georges Chaudet)去世。沃拉德一直通过肖德购买高更的画作,现在直接与高更达成协议。该协议为高更提供了每月 300 法郎的定期预付款,以保证每年以每幅 200 法郎的价格购买至少 25 幅未见过的画作,此外沃拉德还承诺向他提供他的艺术材料。双方最初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高更终于实现了他长期以来在马克萨斯群岛定居的计划,以寻求一个更原始的社会。他在塔希提岛度过了最后几个月,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当时他招待朋友的慷慨就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没有合适的粘土,高更无法继续他在岛上的陶瓷工作。同样,无法使用印刷机,他不得不在他的图形作品中转向单字处理。这些印刷品的幸存例子相当罕见,并且在拍卖室中的价格非常高。
在此期间,高更与普纳奥亚邻居的女儿帕胡拉(Pau'ura)阿泰保持着关系。高更在帕胡拉十四岁半时开始了这段关系。他与她生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在婴儿时期夭折。另一个,一个男孩,她养大。在马修斯的传记期间,他的后代仍然居住在塔希提岛。帕胡拉拒绝陪高更离开她在普纳奥亚的家人去马克萨斯(早些时候,当他在仅 10 英里外的帕皮提工作时,她离开了他)。当英国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在 1917 年拜访她时,她无法为他提供关于高更的有用记忆,并责备他没有从高更的家人那里带钱来拜访她。
马克萨斯群岛
自从他在塔希提岛的头几个月在帕皮提看到一系列雕刻精美的马克森碗和武器后,高更就制定了他在马克萨斯定居的计划。然而,他发现了一个社会,就像在大溪地一样,已经失去了文化认同。在所有太平洋岛群中,马克萨斯群岛受西方疾病(尤其是肺结核)输入的影响最大。 18 世纪的人口约 80,000 人已下降到仅 4,000 人。天主教传教士占主导地位,为了控制醉酒和滥交,他们强迫所有本土儿童在十几岁时就读传教士学校。法国的殖民统治是由一个以恶毒和愚蠢著称的宪兵执行的,而西方和中国的商人则可怕地剥削当地人。
高更于 1901 年 9 月 16 日抵达希瓦瓦岛(Hiva-Oa) 上的阿图奥纳(Atuona) 。这是该岛群的行政首府,但远不如帕皮提发达,尽管两者之间有高效且定期的轮船服务。有军医,但没有医院。医生于次年 2 月迁往帕皮提,此后高更不得不依赖岛上的两名医护人员,除了神学之外,他还学习了医学。这两个人都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他从天主教传教部购买了镇中心的一块土地,首先通过定期参加弥撒来讨好当地主教。这位主教是约瑟夫·马丁 (Monseigneur Joseph Martin),最初对高更有好感,因为他知道高更在他的新闻工作中站在塔希提岛的天主教党一边。
高更在他的地块上建造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足够坚固,能够在后来的飓风中幸存下来,飓风冲走了镇上大多数其他住宅。他在岛上两位最好的马奎桑(Marquesan)木匠的帮助下完成了这项任务,其中一位名叫蒂奥卡(Tioka),以传统的马奎桑方式从头到脚纹身(这一传统被传教士压制)。蒂奥卡是维尼埃会众中的执事,在飓风过后,高更将自己房屋的一角送给他,成为高更的邻居。一楼是露天的,用来吃饭和生活,而顶层是用来睡觉和作为他的工作室。通往顶层的门上装饰着多色木雕门楣和侧壁,至今仍保存在博物馆中。门楣写着这座房子的名字为“快乐之家”(Maison du Jouir),而门框则与他1889年早期的木雕《即恋爱,你会幸福》(Soyez Amoureus vous serez heureuses)相呼应。墙壁上装饰着他珍贵的45张色情照片,这些照片是他从法国出发时在赛义德港购买的。
至少在早期,直到高更发现了瓦赫尼,这所房子在晚上吸引了当地人的赞赏,他们来盯着照片看半夜。毋庸置疑,这一切都没有让高更受到主教的喜爱,更不用说高更在他的台阶脚下竖立了两座雕塑,讽刺主教和一个被称为主教情妇的仆人,更不用说高更后来袭击了不受欢迎的传教士学校系统。主教佩拉德 (Père Paillard) 的雕塑将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展出,而其吊坠件在 2015 年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 30,965,000 美元成交。根据死后的清单,这些是装饰房子的至少八件雕塑之一,其中大部分今天丢失了。他们一起代表了对教会在性问题上虚伪的公开攻击。
由于 1901 年在整个法兰西帝国颁布的协会法案,国家对传教士学校的资助已停止。学校作为私立机构继续面临困难,但当高更确定任何特定学校的出勤率仅在半径约两英里半的流域内是强制性的时,这些困难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这导致许多十几岁的女儿被学校退学(高更称这个过程为“拯救”)。他把一个这样的女孩瓦奥霍(Vaeho,也叫玛丽-罗斯)当作了自己女人(vahine),她是一对本地夫妇的 14 岁女儿,他们住在 6 英里外的一个毗邻的山谷里。这对她来说几乎不是一项愉快的任务,因为高更的疮在那时非常有害,需要每天换药。尽管如此,她心甘情愿地和他住在一起,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她的后代继续住在岛上。
到 11 月,他和瓦奥霍(Vaeho)、一名厨师(Kahui)、另外两名仆人(蒂奥卡的侄子)、他的狗佩高(Pegau)和一只猫安顿下来。房子本身虽然位于镇中心,但却被树木掩映,与外界隔绝。聚会停止了,他开始了一段富有成效的工作,次年四月,他向沃拉德寄出了 20 幅画布。他原以为他会在马克萨斯找到新的主题,他写信给蒙弗雷德:
我认为在马克萨斯,在那里很容易找到模特(这在塔希提岛变得越来越困难),并且有新的国家可以探索——简而言之,有新的、更野蛮的题材——我会做美丽的事情。在这里,我的想象力开始冷却,然后公众也逐渐习惯了塔希提岛。世界是如此愚蠢,如果向它展示包含新的可怕元素的画布,塔希提岛将变得易于理解和迷人。因为塔希提岛,我的布列塔尼作品现在变成了玫瑰水,大溪地将因为马克萨斯而成为古龙水。
— 保罗·高更,1901 年 6 月给乔治·丹尼尔·德·蒙弗雷德的信
事实上,他的马克萨斯(Marquesas )作品大部分只能通过专家或日期来与他的塔希提岛作品区分开来,例如两个女人的画作在他们的位置上仍然不确定。对于安娜·谢赫(Anna Szech) 来说,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平静和忧郁,尽管包含不安的元素。因此,在两个版本的《沙滩上的骑手》中的第二个版本中,云雾缭绕和泡沫破浪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而两个远处的灰马人物则与其他象征死亡的画作中的相似人物相呼应。
高更此时选择画风景、静物和人物研究,着眼于沃拉德的客户,避免他的塔希提岛绘画中原始和失落的天堂主题。但是上一时期的三张重要作品表明了更深层次的担忧。其中前两个是《有扇子的女孩》和 《戴红披风的马克萨斯人》。 年轻女子的模特是红头发的托霍陶瓦(Tohotaua),她是邻近岛屿上一位酋长的女儿。男巫师的模特可能是 哈普阿尼(Haapuani),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舞者,也是一位令人畏惧的魔术师,他是高更的密友,据丹尼尔森(Danielsson) 说,他娶了托霍陶瓦(Tohotau)。托霍陶瓦裙子的白色是波利尼西亚文化中权力和死亡的象征,这位模特为整个濒临灭绝的毛希文化尽责。 第二幅似乎是在同一时间绘制的,描绘了一个穿着异国情调的红色斗篷的长发年轻人。该图像的雌雄同体性质引起了批评,人们猜测高更打算描绘摩诃(māhū,即第三性别的人)。三人组的第三张照片是神秘而美丽的《野蛮人的故事》在右边再次出现了托霍陶瓦(Tohotau)。左边的人物是梅耶·德·哈恩,他是高更在阿文桥时代的画家朋友,几年前去世。而中间的人物又是雌雄同体,佛陀般的姿势和莲花暗示,这幅画是对生命永恒循环和重生可能性的沉思。当这些画作在高更突然去世后到达沃拉德时,人们对高更绘制这些画的意图一无所知。
1902年3月,法属波利尼西亚总督爱德华·佩蒂特( Édouard Petit)抵达马克萨斯进行视察。他由爱德华·查理尔( Édouard Charlier) 陪同担任司法系统的负责人。查理尔是一位业余画家,1895 年他第一次来到帕皮提担任地方法官时,就与高更成为了朋友。然而,当查理尔拒绝起诉高更当时的瓦赫尼·波乌拉犯下的一些琐碎罪行时,他们的关系变成了敌意,据称是入室盗窃和盗窃,当高更不在帕皮提工作时,她在普纳奥亚犯了罪。高更甚至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攻击查理尔关于黄蜂( Les Guêpes) 事件。佩蒂特,大概是适当地预先警告过,拒绝看到高更表达定居者对令人反感的税收制度的抗议(高更是他们的发言人),其中大部分收入来自马克萨斯在帕皮提。高更在 4 月做出回应,拒绝缴纳税款,并鼓励定居者、商人和种植者也这样做。
大约在同一时间,高更的健康再次开始恶化,再次出现同样熟悉的一系列症状,包括腿痛、心悸和全身虚弱。他受伤的脚踝疼痛难以忍受,7 月,他不得不从帕皮提订购一个马车,以便他可以在镇上四处走动。到了 9 月,疼痛非常严重,以至于他不得不注射吗啡。他的视力也开始衰退,正如他在最后一张已知自画像中戴的眼镜所证明的那样。这实际上是他的朋友阮文锦(Ky Dong)自己开始的一幅肖像,他自己完成了,因此它的风格与众不同。它显示了一个人疲惫和衰老,但还没有完全被打败。有一段时间他考虑回到欧洲,去西班牙接受治疗。蒙弗雷德劝告他:
在返回时,您将冒着破坏公众对您的赞赏的孵化过程的风险。目前,您是一位独特而传奇的艺术家,从遥远的南海向我们发送令人不安和无法模仿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一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伟人的最终创作。你的敌人——就像那些让平庸感到不安的人一样,你有很多敌人——沉默。但他们不敢攻击你,想都别想。你离得那么远。你不应该回来……你已经和所有伟大的死者一样无懈可击,你已经属于艺术史了。
— 乔治·丹尼尔·蒙弗雷德,1902 年 10 月左右写给保罗·高更的信
1902 年 7 月,怀有七个月身孕的瓦奥霍(Vaeoho) 离开高更回到她邻近的 山谷,与家人和朋友一起生孩子。她在九月份生了孩子,但没有回来。高更随后没有再接再厉。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与马丁主教关于传教士学校的争吵达到了顶峰。当地宪兵德西雷·夏皮耶 (Désiré Charpillet) 起初对高更友好,他向居住在邻近努库希瓦岛的岛群管理员写了一份报告,批评高更鼓励当地人让孩子辍学并鼓励定居者扣留他们的税款。幸运的是,行政长官的职位最近由高更的老朋友弗朗索瓦·皮克诺 (François Picquenot) 担任,他是来自塔希提岛的高更 (Gauguin) 的老朋友,基本上对他表示同情。皮克诺建议夏皮耶不要对学校问题采取任何行动,因为高更有法律支持他,但授权夏皮耶从高更没收货物以代替缴纳税款,如果一切都失败了。可能是由于孤独,有时无法绘画,高更开始写作。
同年 5 月 27 日,南十字星(Croix du Sud) 号轮船在阿帕塔基环礁附近遭遇海难,该岛有三个月没有邮件或补给。邮件服务恢复后,高更在一封公开信中对珀蒂州长进行了愤怒的攻击,抱怨他们在海难后被遗弃的方式。这封信是由《黄蜂》(Les Guêpes) 的继任报纸《独立》(L'Indepéndant ) 于同年 11 月在帕皮提出版的。事实上,佩蒂特奉行了独立和支持本土的政策,令罗马天主教党感到失望,报纸正准备对他进行攻击。高更还将这封信寄给了法兰西美居酒店,后者在他死后出版了一份经过编辑的版本。随后,他给帕皮提宪兵队的负责人写了一封私信,抱怨他当地的宪兵夏皮勒过度强迫囚犯为他劳作。 虽然这些和类似的抱怨是有根据的,但它们的动机都是虚荣心和单纯的仇恨。碰巧的是,那年 12 月,相对支持的夏皮耶被另一名来自塔希提岛的宪兵让 - 保罗·克拉弗里 (Jean-Paul Claverie) 所取代,他对高更的态度远不如前任。
12 月,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几乎无法绘画。他开始撰写自传体回忆录,他称之为 《之前和之后》(Avant et après),并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完成。这个标题应该反映他来塔希提岛前后的经历,并向他自己的祖母未出版的回忆录过去和未来致敬。事实证明,他的回忆录是对波利尼西亚生活、他自己的生活以及对文学和绘画的评论的零散观察集。他在其中包括对当地宪兵、马丁主教、他的妻子梅特和丹麦人等各种不同主题的攻击,并在总结中描述了他的个人哲学,他认为生活是一场存在主义斗争,以调和对立的二元论。马修斯指出两个结束语是对他哲学的提炼:
没有人是好的,没有人是邪恶的,每个人都是两者,以相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方式。 …
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人的生命,但仍有时间做伟大的事情,共同任务的碎片。
— 保罗·高更,《私密日记》,1903 年
他将手稿寄给方丹纳斯进行编辑,但在高更死后版权归梅特所有,直到 1918 年才出版(传真版); 1921 年出现的美国译本。
死亡
1903 年初,高更发起了一场运动,旨在揭露岛上宪兵的无能,尤其是让-保罗·克拉维里 (Jean-Paul Claverie) 在涉及一群人涉嫌酗酒的案件中直接站在当地人一边。然而,克拉维里逃脱了谴责。 2 月初,高更写信给行政长官弗朗索瓦·皮克诺 (François Picquenot),指控克拉维里 (Claverie) 的一名下属腐败。 皮克诺调查了这些指控,但无法证实这些指控。克拉维里的回应是对高更提出诽谤宪兵的指控。随后,他于 1903 年 3 月 27 日被当地地方法官处以 500 法郎的罚款和三个月的监禁。高更立即提出上诉,并着手筹集资金前往帕皮提听取他的上诉。
此时高更身体虚弱,痛苦万分,再次使用吗啡。他于 1903 年 5 月 8 日早上突然去世。
早些时候,他派他的牧师保罗·维尼尔 (Paul Vernier) 来,抱怨他晕倒了。他们一起聊了聊,相信他的情况已经稳定了。然而,高更的邻居蒂奥卡在 11 点钟发现他死了,通过咀嚼他的头试图让他复活,以传统的马克桑方式证实了这一事实。在他的床边放着一瓶空的劳丹脂,这让人猜测他是服药过量的受害者。有人认为他死于心脏病发作。
直到 1903 年 8 月 23 日,高更去世的消息才传到法国。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他的价值较低的遗产在阿图纳拍卖,而他的信件、手稿和绘画于 1903 年 9 月 5 日在帕皮提拍卖。马修斯注意到他的影响的这种迅速传播导致了关于他晚年的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的丢失。汤姆森指出,他的作品拍卖清单(其中一些被当作色情作品烧毁)揭示了他的生活并不像他喜欢的那样贫穷或原始。梅特·高更(Mette Gauguin)适时收到了拍卖所得,约 4,000 法郎。在帕皮提拍卖的其中一幅画作是《母性(二)》,它是 埃尔米塔日博物馆(Hermitage) 中《母性I》(Maternité I ) 的缩小版。原作是在他当时他们的儿子埃米尔(Emile) 降生时绘制的。不知道他为什么画了较小的副本。这幅画以 150 法郎的价格卖给了法国海军军官科钦司令,他说佩蒂特州长本人为这幅画出价高达 135 法郎。它于 2004 年在苏富比以 39,208,000 美元的价格售出。
2014 年,法医对高更家附近一口井的玻璃罐中发现的四颗牙齿进行了法医检查,对高更患有梅毒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 DNA 检查确定这些牙齿几乎可以肯定是高更的牙齿,但没有发现当时用于治疗梅毒的汞的痕迹,这表明高更没有患有梅毒,或者他没有接受治疗。 2007 年,考古学家在高更在马奎斯群岛的希瓦奥岛建造的一口井底部发现了四颗可能是高更的腐烂臼齿。
历史意义
原始主义是 19 世纪后期绘画和雕塑的艺术运动,其特点是夸张的身体比例、动物图腾、几何图案和鲜明的对比。第一位系统地使用这些效果并在公众中取得广泛成功的艺术家是保罗·高更。欧洲文化精英第一次发现非洲、密克罗尼西亚和美洲原住民的艺术,被这些遥远地方的艺术所体现的新奇、狂野和鲜明的力量所吸引、着迷和教育。就像 20 世纪初的巴勃罗·毕加索一样,高更的灵感和动力来自那些外国文化所谓的原始艺术的原始力量和简单性。
高更也被认为是后印象派画家。他大胆、色彩丰富且以设计为导向的绘画对现代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20 世纪早期受他启发的艺术家和运动包括文森特·梵高、亨利·马蒂斯、巴勃罗·毕加索、乔治·布拉克、安德烈·德兰、野兽派、立体主义和奥菲斯主义等。后来,他影响了亚瑟·弗兰克·马修斯和美国工艺美术运动。
约翰·雷瓦尔德 (John Rewald) 被公认为 19 世纪后期艺术领域的权威,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后印象派画家的书籍时期,包括后印象派:从梵高到高更(1956 年)和一篇文章,保罗·高更:给安布罗斯·沃拉德和安德烈·丰泰纳斯的信(收录于雷瓦尔德的后印象派研究,1986 年),讨论了高更在塔希提岛的岁月和斗争通过与艺术品经销商沃拉德和其他人的通信可以看出他的生存情况。
对毕加索的影响
高更于 1903 年在巴黎秋季沙龙举办的死后回顾展,以及 1906 年更大的回顾展,对法国先锋派,尤其是巴勃罗·毕加索的画作产生了惊人而强大的影响。 1906 年秋天,毕加索创作了超大的裸体女性和不朽的雕塑人物画,让人想起保罗·高更的作品,表现出他对原始艺术的兴趣。毕加索 1906 年的巨幅人物画直接受到高更雕塑、绘画和写作的影响。高更作品所唤起的力量直接导致了 1907 年的 《亚维农少女》。
根据高更传记作者大卫·斯威特曼的说法,毕加索早在 1902 年就在巴黎遇到了西班牙侨民雕塑家兼陶艺家帕科·杜里奥,并成为了高更作品的粉丝。杜里奥手头有几幅高更的作品,因为他是高更的朋友,也是他作品的无偿代理人。杜里奥试图通过在巴黎宣传他的作品来帮助他在大溪地贫困的朋友。在他们见面后,杜里奥向毕加索介绍了高更的粗陶器,帮助毕加索制作了一些陶瓷作品,并给了毕加索第一版《诺亚诺亚:保罗·高更的塔希提岛杂志》。除了在杜里奥那里看到高更的作品,毕加索还在安布罗斯·沃拉德 (Ambroise Vollard )的画廊看到了他和高更的作品。
关于高更对毕加索的影响,约翰·理查森写道:
1906 年的高更作品展让毕加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这位艺术家的束缚。高更展示了最不同类型的艺术——更不用说来自形而上学、民族学、象征主义、圣经、古典神话等等的元素——可以组合成一个既符合时代又永恒的综合体。他证明,一位艺术家还可以通过将他的恶魔驾驭黑暗之神(不一定是大溪地的)并挖掘新的神圣能量来源来混淆传统的美感。如果在晚年毕加索淡化了对高更的亏欠,毫无疑问,在 1905 年至 1907 年间,他与另一位保罗有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后者以从秘鲁祖母那里继承的西班牙基因而自豪。毕加索没有以高更的名义签下自己的“保罗”。
根据理查森的说法,
毕加索在 1906 年秋季沙龙高更回顾展上看到的例子进一步激发了毕加索对粗陶器的兴趣。这些陶瓷中最令人不安的(毕加索可能已经在沃拉德看到过)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奥维里。直到 1987 年,奥赛博物馆收购了这件鲜为人知的作品(自 1906 年以来只展出过一次),它才被公认为是杰作,更不用说因为它与导致少女时代的作品的相关性而被公认为的。虽然只有不到 30 英寸高,但奥维里却有着令人敬畏的存在,就像一座为高更坟墓设计的纪念碑。毕加索对奥维里的印象非常深刻。 50 年后,当库珀和我告诉他我们在一个收藏品中看到了这尊雕塑时,他很高兴,其中还包括他的立体派头部的原始石膏。它是一种启示,就像伊比利亚雕塑一样吗?毕加索耸了耸肩,勉强表示肯定。他总是不愿意承认高更在让他走上原始主义道路上的作用。
技术和风格
高更最初的艺术指导来自毕沙罗,但这种关系留下的印象更多是个人而非风格。高更的大师是乔托、拉斐尔、安格尔、欧仁德拉克洛瓦、马奈、德加和塞尚。他自己的信仰,在某些情况下,他作品背后的心理学也受到哲学家亚瑟·叔本华和诗人斯蒂芬·马拉美的影响。
高更,就像他同时代的一些人一样埃德加·德加和图卢兹·罗特列克,采用了一种在画布上绘画的技术,称为汽油喷漆。为此,油从油漆中排出,剩余的颜料淤泥与松节油混合。他可能使用了类似的技术来准备他的单字,使用纸而不是金属,因为它会吸收油,使最终图像具有他想要的哑光外观。他还在玻璃的帮助下校对了他现有的一些图纸,用水彩或水粉将下面的图像复制到玻璃表面上进行印刷。高更的木刻作品同样具有创新性,即使对于当时负责木刻复兴的前卫艺术家来说也是如此。高更最初不是为了制作详细的插图而切割他的块,而是以类似于木雕的方式雕刻他的块,然后使用更精细的工具在他大胆的轮廓中创造细节和色调。他的许多工具和技术都被认为是实验性的。这种方法和空间的使用与他的平面装饰性浮雕画平行。
从马提尼克岛开始,高更开始在附近使用类似的颜色来实现柔和的效果。此后不久,他也在非具象色彩上取得突破,创作出具有独立存在和生命力的画布。表面现实和他自己之间的这种差距使毕沙罗不高兴,并迅速导致他们的关系结束。他此时的人物形象也提醒着他对日本版画的热爱,尤其是他们人物的天真和构图的朴素对他原始宣言的影响。正因为如此,高更也受到了民间艺术的启发。他寻求以直截了当的方式传达的主题的纯粹情感,强调主要形式和直立的线条以明确定义形状和轮廓。高更还在抽象的图案中使用了精致的正式装饰和色彩,试图协调人与自然。他对自然环境中的原住民的描绘经常表现出宁静和自给自足的可持续性。这赞美了高更最喜欢的主题之一,即超自然现象对日常生活的侵入。
在 1895 年 3 月 15 日出版的《巴黎之声》的采访中,高更解释说,他不断发展的战术方法是达到联觉。他说:
我画中的每一个特征都是事先经过仔细考虑和计算的。就像在音乐作品中一样,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从日常生活或自然中取材的简单对象只是一个借口,它通过一定的线条和颜色的排列来帮助我创造交响乐和和声。他们在现实中根本没有对应物,在那个词的粗俗意义上;它们不直接表达任何想法,它们的唯一目的是激发想象力——就像音乐不需要想法或图片的帮助一样——仅仅通过颜色和线条的某些安排与我们的思想之间存在的神秘亲和力。
在 1888 年给埃米尔·舒芬尼克的一封信中,高更解释了他从印象派迈出的巨大一步,他现在致力于捕捉大自然的灵魂、古老的真理以及风景和居民的特征。高更写道:
不要从字面上复制自然。艺术是一种抽象。当你在大自然面前做梦时,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更多地考虑创造的行为而不是结果。
遗产
高更的作品在他死后不久就开始流行起来。他后来的许多画作都被俄罗斯收藏家谢尔盖·舒金 (Sergei Shchukin) 收购。他的大部分藏品都陈列在普希金博物馆和冬宫。高更画作极少挂牌,上架时在售楼处售价高达数千万美元。他的 1892 年《什么时候嫁人?》成为世界上第三贵的艺术品,当时它的主人 鲁道夫·斯塔赫林(Rudolf Staechelin )家族于 2014 年 9 月以 2.1 亿美元的价格私下将其出售。据信买家是卡塔尔博物馆.
高更的生活启发了萨默塞特·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Mario Vargas Llosa) 以他 2003 年的小说《达标之路》(The Way to Par) 为基础关于高更的生活,以及他的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的生活。
演员安东尼·奎因在 1956 年梵高传记片《欲望人生》中饰演高更,并因其表演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奥斯卡·艾萨克在后来的梵高传记片《永恒之门》中饰演高更。弗拉基米尔·约达诺夫在 1990 年的电影《文森特与提奥》中饰演高更。
日式风格的高更博物馆位于塔希提岛帕皮里的帕皮里植物园对面,收藏有高更和大溪地人的一些展品、文件、照片、复制品以及原始草图和版画。 2003 年,保罗·高更文化中心在马克萨斯群岛的阿图纳开业。
2014 年,在意大利发现了 1970 年在伦敦失窃的画作《桌上的水果》(1889 年),估价在 1000 万至 3000 万欧元(830 万至 2480 万英镑)之间。这幅画连同皮埃尔·博纳尔 (Pierre Bonnard) 的作品于 1975 年由一名菲亚特员工在铁路失物招领中以 45,000 里拉(约合 32 英镑)的价格购买。
生卒日期: 1848年6月7日 - 1903年5月8日
国籍:法国
保罗·高更的全部作品(611)
欧仁·亨利·保罗·高更(Eugène Henri Paul Gauguin)是法国后印象派艺术家。直到他死后才被人欣赏,高更现在因其对色彩和与印象派不同的合成风格的实验性使用而受到认可。在他生命的尽头,他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度过了十年。这个时期的绘画描绘了那个地区的人物或风景。
他的作品影响了法国前卫和许多现代艺术家,如毕加索和亨利·马蒂斯,他以与文森特·梵高和西奥·梵高的关系而闻名。高更的艺术在他去世后开始流行,部分原因是经销商安布罗斯·沃拉德 (Ambroise Vollard) 的努力,他在职业生涯后期组织了他的作品展览,并协助在巴黎组织了两次重要的死后展览。
作为画家、雕塑家、版画家、陶艺家和作家,高更是象征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在景泰蓝风格的影响下,在绘画中表达题材的内在意义,为原始主义和回归田园主义铺平了道路。他也是木雕和木刻作为艺术形式的有影响力的支持者。
家族史和早年生活
高更于 1848 年 6 月 7 日出生在巴黎,其父母为克洛维斯·高更 (Clovis Gauguin) 和艾琳·查扎尔 (Aline Chazal)。他的出生恰逢同年整个欧洲的革命动荡。他的父亲是一名 34 岁的自由派记者,来自居住在奥尔良的一个企业家家庭。当他为之撰写的报纸被法国当局压制时,他被迫逃离法国。高更的母亲是雕刻家安德烈·查扎尔 (André Chazal) 和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作家和活动家弗洛拉·特里斯坦 (Flora Tristan) 的女儿。当安德烈袭击他的妻子弗洛拉并因谋杀未遂被判入狱时,他们的结合结束了。
保罗·高更的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 Flora Tristan)是泰蕾莎·莱斯奈( Thérèse Laisnay)和唐·马里亚诺·德·特里斯坦·莫斯科索(Don Mariano de Tristan Moscoso)的私生女。 泰蕾莎(Thérèse)的详细家庭背景不得而知,唐·马里亚诺 (Don Mariano) 来自秘鲁阿雷基帕市的一个西班牙贵族家庭。他是龙骑兵的一名军官。富有的特里斯坦莫斯科索家族的成员在秘鲁担任重要职位。尽管如此,唐马里亚诺的意外死亡使他的情妇和女儿弗洛拉陷入贫困。当弗洛拉与安德烈的婚姻失败时,她向她父亲的秘鲁亲戚请愿并获得了一笔小额赔偿金。她航行到秘鲁,希望扩大她在特里斯坦莫斯科索家族财富中的份额。这从未实现,但她成功地出版了一本关于她在秘鲁的经历的流行游记,并于 1838 年开启了她的文学生涯。作为早期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支持者,高更的外祖母为 1848 年的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 1844 年,她被法国警察监视并因过度劳累而去世。她的孙子保罗“崇拜他的祖母,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随身携带她的书”。
1850 年,克洛维斯·高更 (Clovis Gauguin) 带着妻子艾琳 (Aline) 和年幼的孩子前往秘鲁,希望在妻子南美关系的支持下继续他的新闻事业。他在途中死于心脏病,艾琳作为寡妇与 18 个月大的保罗和他的2岁半的姐姐玛丽一起抵达秘鲁。高更的母亲受到她祖父的欢迎,他的女婿不久将担任秘鲁总统。到六岁时,保罗享受着特权的成长,有保姆和仆人陪伴。他保留了童年时期的生动记忆,这给他灌输了“无法磨灭的秘鲁印象,困扰着他的余生”。
1854 年秘鲁内战期间,当他的家庭支柱跟随政治权力机构倒台时,高更田园诗般的童年戛然而止。艾琳带着她的孩子返回法国,将保罗与他的祖父纪尧姆·高更留在奥尔良。秘鲁特里斯坦莫斯科索家族剥夺了她的外祖父安排的丰厚年金,艾琳在巴黎定居,担任裁缝。
教育和第一份工作
在参加了当地的几所学校后,高更被送到了著名的天主教寄宿学校拉夏贝尔圣梅斯敏小修院。他在学校待了三年。 14 岁时,他进入巴黎的洛里奥尔学院(Loriol Institute),这是一所海军预备学校,然后返回奥尔良,在圣女贞德中学度过他的最后一年。高更签约成为商船的驾驶员助理。三年后,他加入法国海军,服役两年。他的母亲于 1867 年 7 月 7 日去世,但几个月后他才知道这件事,直到他姐姐玛丽的一封信赶上了在印度的高更。
1871 年,高更回到巴黎,在那里找到了一份股票经纪人的工作。一位亲密的家庭朋友古斯塔夫·阿罗萨 (Gustave Arosa) 让他在巴黎证券交易所找到了一份工作;高更 23 岁。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巴黎商人,并在接下来的 11 年里一直保持着这一地位。 1879 年,他作为一名股票经纪人每年赚取 30,000 法郎(按 2019 年美元计算约为 145,000 美元),在他在艺术市场的交易中再次获得同样的收入。但在 1882 年,巴黎股市崩盘,艺术品市场萎缩。高更的收入急剧下降,他最终决定全职从事绘画。
婚姻
1873 年,他与丹麦妇女 梅特-索菲·盖德(Mette-Sophie Gad,1850–1920) 结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们有五个孩子:埃米尔(Émile,1874-1955)、艾琳 (Aline,1877–1897)、克洛维斯 (Clovis,1879–1900)、让·勒内 ( Jean René,1881–1961)、和保罗·罗伦 ( Paul Rollon,1883–1961)。到 1884 年,高更与家人搬到丹麦哥本哈根,在那里他从事防水布推销员的商业生涯。这并不成功:他不会说丹麦语,而且丹麦人不想要法国防水油布。梅特成为主要的养家糊口的人,为见习外交官提供法语课程。
当高更被迫从事全职绘画工作 11 年后,他的中产阶级家庭和婚姻破裂了。 1885 年,在他的妻子和她的家人要求他离开之后,他回到了巴黎,因为他已经放弃了他们共同的价值观。高更与他们最后一次身体接触是在 1891 年,梅特最终在 1894 年果断地与他决裂。
第一幅画
1873 年,大约在他成为股票经纪人的同时,高更开始在空闲时间画画。他的巴黎生活以巴黎第九区为中心。高更住在 布鲁耶尔街(rue la Bruyère)15号。附近是印象派画家经常光顾的咖啡馆。高更还经常参观画廊并购买新兴艺术家的作品。他与毕沙罗 建立了友谊,并在星期天拜访他,在他的花园里作画。毕沙罗向他介绍了其他各种艺术家。 1877 年,高更“搬到了低端市场,穿过河流,搬到了更贫穷、更新的城市蔓延”沃吉拉尔。在这里三楼,他有第一个拥有工作室的家。
他的密友埃米尔·舒芬尼克住在附近,他曾是一名股票经纪人,也渴望成为一名艺术家。高更在 1881 年和 1882 年举办的印象派展览中展示了绘画。他的画作受到了不屑一顾的评价,尽管其中一些,例如《沃吉拉德的市场花园》,现在受到高度评价。
1882 年,股市崩盘,艺术品市场萎缩。印象派的主要艺术品经销商保罗·杜兰德-鲁埃尔 (Paul Durand-Ruel) 受崩盘的影响尤其严重,并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从高更等画家那里购买画作。高更的收入急剧下降,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慢慢制定了成为全职艺术家的计划。接下来的两个夏天,他与毕沙罗一起画画,偶尔也与保罗·塞尚一起画画。
1883 年 10 月,他写信给毕沙罗,说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以绘画为生,并寻求他的帮助,而毕沙罗起初欣然提供了帮助。次年一月,高更与家人搬到鲁昂,在那里他们可以住得更便宜,而且他认为他在去年夏天访问毕沙罗时发现了机会。然而,这次冒险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到年底,梅特和孩子们搬到了哥本哈根,之后不久于 1884 年 11 月,高更带着他的艺术收藏品,随后留在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的生活同样艰难,他们的婚姻也变得紧张起来。在梅特的敦促和家人的支持下,高更于次年返回巴黎。
法国 1885–1886
1885 年 6 月,高更在他 6 岁的儿子克洛维斯的陪同下返回巴黎。其他孩子留在哥本哈根的梅特身边,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家人和朋友的支持,而梅特本人则能够找到翻译和法语教师的工作。高更最初发现很难重新进入巴黎的艺术界,并在真正的贫困中度过了他的第一个冬天,不得不从事一系列卑微的工作。克洛维斯最终病倒并被送到寄宿学校,高更的姐姐玛丽提供了资金。在第一年,高更创作的艺术作品很少。 1886 年 5 月,他在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印象派展览上展出了 19 幅画作和一幅木浮雕。
这些画作大多是鲁昂或哥本哈根的早期作品,尽管他的《女人洗澡》引入了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即海浪中的女人,但在少数新作品中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新奇。尽管如此,Félix Bracquemond确实购买了他的一幅画。此次展览还确立了乔治·修拉作为巴黎前卫运动的领导者的地位。高更轻蔑地拒绝了修拉的新印象派点彩画技巧,并在今年晚些时候果断地与毕沙罗决裂,从那时起,毕沙罗对高更颇为敌视。
1886 年夏天,高更在布列塔尼的阿文桥艺术家殖民地度过。他之所以被吸引,首先是因为住在那里很便宜。然而,他发现自己在夏天涌入那里的年轻艺术学生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天生好斗的气质(他既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拳击手又是击剑手)在社交轻松的海滨度假胜地没有任何障碍。在那个时期,他的古怪外表和他的艺术都被人们铭记。在这些新同事中,Charles Laval将在次年陪同高更前往巴拿马和马提尼克岛。
那年夏天,他以毕沙罗(Pissarro)和德加(Degas)在 1886 年第八届印象派展览上展出的方式绘制了一些裸体人物的粉彩画。他主要画风景如《布雷顿牧羊女》,其中人物扮演次要角色。他的《布列塔尼男孩洗澡》介绍了他每次访问阿文桥时都会回到的主题,显然要感谢埃德加·德加的设计和对纯色的大胆使用。英国插画家Randolph Caldecott的天真画作曾用于描绘一本关于布列塔尼的流行指南,吸引了阿文桥 (Pont-Aven) 前卫学生艺术家的想象力,他们渴望摆脱学院派的保守主义,而高更 (Gauguin)有意识地在他的布列塔尼女孩素描中模仿它们。这些草图后来在他的巴黎工作室被加工成画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四个布雷顿女人》,它与他早期的印象派风格明显不同,并融入了凯迪克插图的天真品质,将特征夸大到了漫画的地步。
高更与埃米尔·伯纳德、Charles Laval、埃米尔·舒芬尼克和其他许多人在巴拿马和马提尼克岛旅行后重新访问了阿文桥。纯色的大胆使用和象征主义题材的选择区分了现在所谓的阿文桥派( Pont-Aven School)。对印象派失望的高更觉得欧洲传统绘画过于模仿,缺乏象征深度。相比之下,非洲和亚洲的艺术在他看来充满了神秘的象征意义和活力。当时欧洲流行其他文化的艺术,尤其是日本(日本主义)的艺术。 1889年应邀参加二十(Les XX)组织的展览。
分割主义(Cloisonnism,又名景泰蓝主义)和综合主义( synthetism,又名合成主义)
在民间艺术和日本版画的影响下,高更的作品向分割主义方向发展,这种风格由评论家爱德华·杜雅尔丹(Édouard Dujardin)命名,用来描述埃米尔·伯纳德(Émile Bernard)的色彩平坦区域和大胆轮廓的绘画方法,使杜雅尔丹想起中世纪的景泰蓝珐琅技术。高更非常欣赏伯纳德的艺术以及他大胆采用适合高更的风格来表达他的艺术作品的本质。
在高更的《黄色的基督》中,这幅画经常被引用为景泰蓝主义的典型作品,图像被简化为由浓黑轮廓分隔的纯色区域。在这样的作品中,高更很少注意古典透视,大胆地消除了微妙的色彩层次,从而摒弃了文艺复兴后绘画的两个最典型的原则。他的绘画后来演变为合成主义,其中形式和色彩均不占主导地位,但两者均具有同等作用。
马提尼克
1887 年,在访问了巴拿马之后,高更于 6 月至 11 月在加勒比海马提尼克岛的圣皮埃尔( Saint Pierre)附近度过,并由他的朋友艺术家Charles Laval陪同。他在这段时间的想法和经历都记录在他给妻子梅特(Mette)和他的艺术家朋友埃米尔·舒芬尼克的信中。他通过巴拿马到达马提尼克岛,在那里他发现自己破产了,没有工作。当时法国有一项遣返政策,如果公民破产或滞留在法国殖民地,国家将支付回程费用。离开巴拿马后,在遣返政策的保护下,高更和拉瓦尔决定在马提尼克岛的圣皮埃尔港下船。对于高更是有意还是自发决定留在岛上,学者们意见不一。
起初,他们住的“黑人小屋”很适合他,他喜欢观察人们的日常活动。然而,夏天的天气很热和小屋在雨中漏水了。高更还患上了痢疾和沼泽热。在马提尼克岛期间,他创作了 10 到 20 部作品(最常见的估计是 12 部),广泛旅行,显然与一小群印度移民接触过,这种接触后来通过融入印度符号影响了他的艺术。在他逗留期间,作家拉夫卡迪奥·赫恩( Lafcadio Hearn)也在岛上。他的叙述提供了一个历史比较以配合高更的图像。
高更在马提尼克岛逗留期间完成了 11 幅著名的画作,其中许多似乎来自他的小屋。他写给埃米尔·舒芬尼克的信表达了对他画作中所代表的异国情调和当地人的兴奋。高更断言,他在岛上的四幅画作比其他画作更好。作品整体色彩鲜艳,画松散,户外人物场景。虽然他在岛上的时间很短,但肯定是有影响的。他在后来的画作中回收了他的一些人物和草图,例如在他的粉丝身上复制的芒果中的主题。高更离开该岛后,农村和土著居民仍然是高更作品中的热门主题。
文森特和提奥·梵高
高更的马提尼克岛画作在他的颜料商人阿尔塞纳·普瓦捷(Arsène Poitier) 的画廊展出。在那里,文森特·梵高和他的艺术品经销商兄弟提奥看到并钦佩他们。西奥以 900 法郎的价格购买了高更的三幅画,并安排将它们挂在古皮家,从而将高更介绍给了富有的客户。在 1891 年提奥去世后,古比尔的这种安排仍在继续。同时,文森特和高更成为了亲密的朋友,他们一起在艺术上通信,这种通信有助于高更制定他的艺术哲学。
1888 年,在提奥的怂恿下,高更和文森特在法国南部阿尔勒的文森特黄屋共画了九周。高更与文森特的关系令人担忧。他们的关系恶化,最终高更决定离开。 1888 年 12 月 23 日晚上,根据后来对高更的描述,文森特用一把直剃刀对着高更。当天晚上晚些时候,他割掉了自己的左耳。他用报纸把切下的耳朵包起来,送给在高更和文森特都去过的妓院工作的一位女士,并要求她“小心保管这件物品,以纪念我”。第二天文森特住院,高更离开了阿尔勒。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继续通信,1890 年,高更甚至提议他们在安特卫普成立一个艺术家工作室。 1889 年的雕塑自画像《头形壶》(Jug in the Form of a Head )似乎参考了高更与文森特的创伤关系。
高更后来声称在影响文森特·梵高作为阿尔勒画家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文森特在《埃顿花园的记忆》等画作中对高更的“从想象中绘画”的理论进行了简短的实验,但这并不适合他,他很快又回到了从自然中绘画。
埃德加·德加
尽管高更在毕沙罗的领导下在艺术界取得了一些早期的进步,但埃德加·德加是高更最受尊敬的当代艺术家,从一开始就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人物和室内设计以及歌手的雕刻和彩绘奖章瓦莱丽·鲁米。他对德加的艺术尊严和机智深怀敬意。这是高更最健康、最持久的友谊,贯穿了他的整个艺术生涯,直到他去世。
德加成为他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亲自购买高更的作品并说服经销商保罗·杜兰德-鲁埃尔也这样做,没有谁比德加更坚定地公开支持高更了。高更还在 1870 年代早期到中期从德加那里购买了作品,他自己的单一类型倾向可能受到德加在媒介方面的进步的影响。
1893 年 11 月,德加主要组织的高更的杜朗-鲁埃尔(Durand-Ruel)展览收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嘲笑者包括克劳德·莫奈、雷诺阿和前朋友毕沙罗。然而,德加称赞了他的作品,购买了《我停下》并欣赏高更变幻出的民间传说的异国奢华。作为欣赏,高更向德加赠送了《月亮和地球》,这是曾引起最敌对批评的展出画作之一。高更的油画《沙滩上的骑手》(两个版本)回忆德加在 1860 年代开始的马匹主题绘画,特别是《赛前》,证明了他对高更的持久影响。德加后来在高更 1895 年的拍卖会上购买了两幅画作,为他最后一次去塔希提岛的旅行筹集资金。这些是 《女人和芒果》和高更画的爱德华·马奈的《奥林匹亚》版本。
第一次去大溪地
到 1890 年,高更构思了将大溪地作为下一个艺术目的地的计划。 1891 年 2 月在巴黎德鲁奥酒店成功拍卖画作,以及宴会和慈善音乐会等其他活动,提供了必要的资金。高更通过毕沙罗向奥克塔夫·米尔博 (Octave Mirbeau) 发表了讨人喜欢的评论,这极大地帮助了拍卖。在哥本哈根探望妻儿后,高更于 1891 年 4 月 1 日启航前往塔希提岛,并承诺返回一个富人并重新开始,这是最后一次。他公开的意图是逃避欧洲文明和“一切人为和传统的东西”。尽管如此,他还是小心翼翼地随身携带了一系列图画、素描和印刷品形式的视觉刺激。
他在殖民地首都帕皮提( Papeete)度过了前三个月,已经深受法国和欧洲文化的影响。他的传记作者贝琳达·汤姆森 (Belinda Thomson) 观察到,他对原始田园诗的想象一定很失望。他无法负担在帕皮提追求享乐的生活方式,早期的肖像画《苏珊班布里奇肖像》并不受欢迎。他决定在距离帕皮提约 45 公里(28 英里)的帕皮阿里马泰亚建立他的工作室,将自己安置在一个本土风格的竹屋里。在这里,他创作了描绘大溪地生活的画作,如《海边》和 《冰冷的玛丽亚》,后者成为他最珍贵的大溪地画作。
他的许多最优秀的画作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他的第一个大溪地模特肖像被认为是 《拿着花的大溪地女人》。这幅画以其描绘波利尼西亚特征的谨慎而著称。他把这幅画寄给了他的赞助人乔治·丹尼尔·德·蒙弗莱德( George-Daniel de Monfreid),他是埃米尔·舒芬尼克的朋友,后者将成为高更在大溪地的忠实拥护者。到 1892 年夏末,这幅画在巴黎古皮尔画廊展出。艺术史学家南希·莫尔·马修斯(Nancy Mowll Mathews)认为,高更在大溪地遇到的异国情调,在这幅画中如此明显,是他在那里逗留的最重要的方面。
高更借了雅克-安托万·莫伦豪特 (Jacques-Antoine Moerenhout) 1837 年的《去大洋群岛旅行》(Voyage aux îles du Grand Océan)和埃德蒙·德博维斯 (Edmond de Bovis) 的 1855 年的《欧洲人到来时的塔希提社会状况》( État de la société tahitienne à l'arrivée des Européens),其中包含对大溪地被遗忘的宗教的完整描述。高更对波利尼西亚社会 (Arioi )和他们的神奥罗(Ora)的叙述着迷。因为这些记载没有插图,而且大溪地的模型反正早就消失了,他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创作了大约二十幅画作和十多幅木雕。其中第一个是《舞蹈种子》,代表奥罗(Oro)在陆地的妻子 瓦劳马蒂(Vairaumati),现在由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他当时的插图笔记本 《古代的崇拜马霍里》(Ancien Culte Mahorie )保存在卢浮宫,并于 1951 年以影印形式出版。
高更总共将他的九幅画寄给了巴黎的蒙弗莱德(Monfreid)。这些作品最终在哥本哈根与已故文森特·梵高的联合展览中展出。他们受到好评的报道(尽管实际上只有两幅大溪地画作售出,而且他早期的画作与梵高的画作相比并不有利)足以鼓舞高更考虑带着他完成的其他七十幅画回来。在任何情况下,他的资金基本上都用完了,这取决于国家对免费回家的补助。此外,他还有一些健康问题,当地医生诊断为心脏问题,马修斯认为这可能是心血管梅毒的早期迹象。
高更后来写了一篇名为《诺阿诺阿》(Noa Noa,1901 年首次出版) 的游记,最初被认为是对他的画作的评论,并描述了他在大溪地的经历。现代评论家认为这本书的内容部分是幻想和抄袭。他在其中透露,此时他娶了一个 13 岁的女孩为本地妻子(vahine,大溪地语中的“女人”),婚姻在一个下午的过程中缔结。这就是特哈阿马纳(Teha'amana) ,在游记中被称为特胡拉(Tehura),她在 1892 年夏末怀孕。 特哈阿马纳是高更几幅画作的主题,包括 《马拉希梅图亚不提哈马纳》和著名的《游魂》,以及现在在奥赛博物馆中的著名木雕《特胡拉》( Tehura)。到 1893 年 7 月末,高更他决定离开塔希提岛,即使几年后返回该岛,他也永远不会再见到特哈阿马纳或她的孩子。
返回法国
1893 年 8 月,高更回到法国,继续创作大溪地题材的画作,如 《神之日》和《神圣的春天,甜蜜的梦》。 1894 年 11 月在杜兰鲁尔画廊举办的展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展出的 40 幅画作中有 11 幅以相当高的价格出售。他在艺术家经常光顾的蒙帕纳斯区边缘的维辛埃托里克斯街(rue Vercingétorix)6号 设立了一套公寓,并开始每周举办一次沙龙。他扮演了一个异国情调的角色,穿着波利尼西亚人的服装,并与一名仍处于十几岁的年轻女子,“半印度半马来亚人”,被称为爪哇人安娜的公开恋情。
尽管他 11 月的展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他随后在不明朗的情况下失去了杜兰·鲁尔(Durand-Ruel )的赞助。马修斯将此描述为高更职业生涯的悲剧。除其他外,他失去了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 1894 年初,他发现他使用实验技术为他提议的游记《诺阿诺阿》(Noa Noa) 准备木刻版画。他在夏天回到了蓬艾文。 1895 年 2 月,他试图在巴黎的德鲁奥酒店(Hôtel Drouot)拍卖他的画作,类似于 1891 年的那幅画,但没有成功。然而,1895 年 3 月,经销商安布罗斯·沃拉德(Ambroise Vollard) 在他的画廊展示了他的画作,但不幸的是,他们当时并没有达成协议。
他向 1895 年 4 月开幕的法国国立美术学院(Société Nationale des Beaux-Arts) 沙龙提交了一件他称之为《野生》(Oviri,大溪地神话中是哀悼女神) 的大型陶瓷雕塑,这是他去年冬天烧制的。关于它的接受方式有不同的版本:他的传记作者和《诺阿诺阿》的合作者,象征主义诗人查尔斯·莫里斯( Charles Morice),争辩说(1920 年)这幅作品被“从字面上驱逐”了展览。无论如何,高更借此机会向晚报写了一封关于现代陶瓷状况的愤怒信,以增加他的公众曝光率。
到这个时候,他和他的妻子梅特已经不可挽回地分居了。虽然有和解的希望,但他们很快就因金钱问题吵架,谁也没有去拜访对方。高更最初拒绝分享他的叔叔伊西多尔 (Isidore) 的 13,000 法郎遗产中的任何部分,这是他回国后不久获得的。梅特最终得到了 1,500 法郎的礼物,但她很生气,从那时起就只通过埃米尔·舒芬尼克与他保持联系——这对高更来说是双重的痛苦,因为他的朋友因此知道他背叛的真实程度。
到 1895 年中期,为高更返回塔希提岛筹集资金的尝试失败了,他开始接受朋友的慈善事业。 1895 年 6 月,尤金·卡里埃 安排了一条廉价通道返回大溪地,高更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欧洲。
住在大溪地
高更于 1895 年 6 月 28 日再次启程前往塔希提岛。这次回归本质上是负面的,他对巴黎艺术界的幻想破灭,在同一期《风雅信使》(Mercure de France)上两次攻击他,一个是埃米尔·伯纳德,另一个是卡米尔·莫克莱尔( Camille Mauclair)的。马修斯评论说,他在巴黎的孤立变得如此痛苦,以至于他别无选择,只能试图重新获得他在大溪地社会中的地位。
他于 1895 年 9 月抵达,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帕皮提附近或有时在帕皮提附近过着看似舒适的艺术家殖民地生活。在此期间,他能够通过越来越稳定的销售流以及朋友和祝福者的支持来养活自己,尽管在 1898 年至 1899 年的一段时间里,他感到不得不在帕皮提从事办公桌工作,其中没有多少记录。他在帕皮提以东十英里的富裕地区普纳奥亚建造了一座宽敞的芦苇和茅草屋,由富裕家庭定居,他在其中安装了一个大工作室,不惜一切代价。朱尔斯·阿戈斯蒂尼(Jules Agostini)是高更的熟人,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业余摄影师,于 1896 年拍摄了这所房子。后来土地出售迫使他在同一个街区建造了一座新房子。
他养了一匹马和马车,因此可以每天前往帕皮提,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参加殖民地的社交生活。他订阅《风雅信使》(Mercure de France),是当时法国最重要的评论期刊,并与巴黎的艺术家、经销商、评论家和赞助人保持着积极的通信。在帕皮提的那一年及此后,他在当地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最近成立的反对殖民政府的当地期刊 《黄蜂》(Les Guêpes,The Wasps)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最终成为月刊的编辑。他的报纸上有一定数量的艺术品和木刻版画幸存下来。 1900 年 2 月,他成为《黄蜂》 的编辑,并为此领取薪水,并继续担任编辑,直到 1901 年 9 月离开塔希提岛。 但实际上并不是本土事业的拥护者,尽管有些人们如此认为。
至少在第一年,他没有创作任何画作,这告诉蒙弗雷德,他打算从此专注于雕塑。他这一时期的木雕很少能幸存下来,其中大部分是蒙弗雷德收集的。当他恢复绘画时,继续他长期存在的一系列充满性感的裸体画作,如《上帝之子》和《永远》。汤姆森观察到复杂性的进展。马修斯注意到基督教象征主义的回归,这会让他受到当时殖民者的喜爱,现在急于通过强调宗教原则的普遍性来保护本土文化的剩余部分。在这些画作中,高更正在解决他的听众是他在帕皮提的殖民者同胞,而不是他以前在巴黎的前卫听众。
他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他因各种疾病多次住院。当他在法国时,他在去孔卡尔诺的海边旅行中因醉酒斗殴而摔断了脚踝。伤口,开放性骨折,从未正确愈合。然后限制他行动的痛苦和虚弱的疮开始在他的腿上上下爆发。这些用砷处理。高更指责热带气候并将疮描述为“湿疹”,但他的传记作者同意这一定是梅毒的进展。
1897 年 4 月,他收到消息,他最喜欢的女儿艾琳死于肺炎。这也是他得知他不得不腾出房子的月份,因为它的土地已经卖掉了。他向银行贷款,建造了一座更加奢华的木屋,享有山景和海景。但他这样做太过分了,到年底时他面临着银行对他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真实前景。健康状况不佳和债务紧迫,使他濒临绝望。年底,他完成了他不朽的作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他认为这是他的杰作和最后的艺术遗嘱,在给乔治·丹尼尔·蒙弗里德的一封信中,他解释说他在完成后试图自杀。这幅画于次年 11 月与他在 7 月之前完成的八幅主题相关的画作一起在沃拉德(Vollard)的画廊展出。这是他自 1893 年杜朗-鲁埃尔展览以来的第一次在巴黎举办的大型展览,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评论家称赞他的新宁静。然而,作品收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沃拉德很难将其出售。他最终在 1901 年以 2,500 法郎(2000 年美元约 10,000 美元)的价格将其卖给了 加布里埃尔·弗里索(Gabriel Frizeau),其中沃拉德的佣金可能高达 500 法郎。
1899 年秋天,高更的巴黎经销商乔治·肖德(Georges Chaudet)去世。沃拉德一直通过肖德购买高更的画作,现在直接与高更达成协议。该协议为高更提供了每月 300 法郎的定期预付款,以保证每年以每幅 200 法郎的价格购买至少 25 幅未见过的画作,此外沃拉德还承诺向他提供他的艺术材料。双方最初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高更终于实现了他长期以来在马克萨斯群岛定居的计划,以寻求一个更原始的社会。他在塔希提岛度过了最后几个月,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当时他招待朋友的慷慨就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没有合适的粘土,高更无法继续他在岛上的陶瓷工作。同样,无法使用印刷机,他不得不在他的图形作品中转向单字处理。这些印刷品的幸存例子相当罕见,并且在拍卖室中的价格非常高。
在此期间,高更与普纳奥亚邻居的女儿帕胡拉(Pau'ura)阿泰保持着关系。高更在帕胡拉十四岁半时开始了这段关系。他与她生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在婴儿时期夭折。另一个,一个男孩,她养大。在马修斯的传记期间,他的后代仍然居住在塔希提岛。帕胡拉拒绝陪高更离开她在普纳奥亚的家人去马克萨斯(早些时候,当他在仅 10 英里外的帕皮提工作时,她离开了他)。当英国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在 1917 年拜访她时,她无法为他提供关于高更的有用记忆,并责备他没有从高更的家人那里带钱来拜访她。
马克萨斯群岛
自从他在塔希提岛的头几个月在帕皮提看到一系列雕刻精美的马克森碗和武器后,高更就制定了他在马克萨斯定居的计划。然而,他发现了一个社会,就像在大溪地一样,已经失去了文化认同。在所有太平洋岛群中,马克萨斯群岛受西方疾病(尤其是肺结核)输入的影响最大。 18 世纪的人口约 80,000 人已下降到仅 4,000 人。天主教传教士占主导地位,为了控制醉酒和滥交,他们强迫所有本土儿童在十几岁时就读传教士学校。法国的殖民统治是由一个以恶毒和愚蠢著称的宪兵执行的,而西方和中国的商人则可怕地剥削当地人。
高更于 1901 年 9 月 16 日抵达希瓦瓦岛(Hiva-Oa) 上的阿图奥纳(Atuona) 。这是该岛群的行政首府,但远不如帕皮提发达,尽管两者之间有高效且定期的轮船服务。有军医,但没有医院。医生于次年 2 月迁往帕皮提,此后高更不得不依赖岛上的两名医护人员,除了神学之外,他还学习了医学。这两个人都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他从天主教传教部购买了镇中心的一块土地,首先通过定期参加弥撒来讨好当地主教。这位主教是约瑟夫·马丁 (Monseigneur Joseph Martin),最初对高更有好感,因为他知道高更在他的新闻工作中站在塔希提岛的天主教党一边。
高更在他的地块上建造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足够坚固,能够在后来的飓风中幸存下来,飓风冲走了镇上大多数其他住宅。他在岛上两位最好的马奎桑(Marquesan)木匠的帮助下完成了这项任务,其中一位名叫蒂奥卡(Tioka),以传统的马奎桑方式从头到脚纹身(这一传统被传教士压制)。蒂奥卡是维尼埃会众中的执事,在飓风过后,高更将自己房屋的一角送给他,成为高更的邻居。一楼是露天的,用来吃饭和生活,而顶层是用来睡觉和作为他的工作室。通往顶层的门上装饰着多色木雕门楣和侧壁,至今仍保存在博物馆中。门楣写着这座房子的名字为“快乐之家”(Maison du Jouir),而门框则与他1889年早期的木雕《即恋爱,你会幸福》(Soyez Amoureus vous serez heureuses)相呼应。墙壁上装饰着他珍贵的45张色情照片,这些照片是他从法国出发时在赛义德港购买的。
至少在早期,直到高更发现了瓦赫尼,这所房子在晚上吸引了当地人的赞赏,他们来盯着照片看半夜。毋庸置疑,这一切都没有让高更受到主教的喜爱,更不用说高更在他的台阶脚下竖立了两座雕塑,讽刺主教和一个被称为主教情妇的仆人,更不用说高更后来袭击了不受欢迎的传教士学校系统。主教佩拉德 (Père Paillard) 的雕塑将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展出,而其吊坠件在 2015 年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 30,965,000 美元成交。根据死后的清单,这些是装饰房子的至少八件雕塑之一,其中大部分今天丢失了。他们一起代表了对教会在性问题上虚伪的公开攻击。
由于 1901 年在整个法兰西帝国颁布的协会法案,国家对传教士学校的资助已停止。学校作为私立机构继续面临困难,但当高更确定任何特定学校的出勤率仅在半径约两英里半的流域内是强制性的时,这些困难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这导致许多十几岁的女儿被学校退学(高更称这个过程为“拯救”)。他把一个这样的女孩瓦奥霍(Vaeho,也叫玛丽-罗斯)当作了自己女人(vahine),她是一对本地夫妇的 14 岁女儿,他们住在 6 英里外的一个毗邻的山谷里。这对她来说几乎不是一项愉快的任务,因为高更的疮在那时非常有害,需要每天换药。尽管如此,她心甘情愿地和他住在一起,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她的后代继续住在岛上。
到 11 月,他和瓦奥霍(Vaeho)、一名厨师(Kahui)、另外两名仆人(蒂奥卡的侄子)、他的狗佩高(Pegau)和一只猫安顿下来。房子本身虽然位于镇中心,但却被树木掩映,与外界隔绝。聚会停止了,他开始了一段富有成效的工作,次年四月,他向沃拉德寄出了 20 幅画布。他原以为他会在马克萨斯找到新的主题,他写信给蒙弗雷德:
我认为在马克萨斯,在那里很容易找到模特(这在塔希提岛变得越来越困难),并且有新的国家可以探索——简而言之,有新的、更野蛮的题材——我会做美丽的事情。在这里,我的想象力开始冷却,然后公众也逐渐习惯了塔希提岛。世界是如此愚蠢,如果向它展示包含新的可怕元素的画布,塔希提岛将变得易于理解和迷人。因为塔希提岛,我的布列塔尼作品现在变成了玫瑰水,大溪地将因为马克萨斯而成为古龙水。
— 保罗·高更,1901 年 6 月给乔治·丹尼尔·德·蒙弗雷德的信
事实上,他的马克萨斯(Marquesas )作品大部分只能通过专家或日期来与他的塔希提岛作品区分开来,例如两个女人的画作在他们的位置上仍然不确定。对于安娜·谢赫(Anna Szech) 来说,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平静和忧郁,尽管包含不安的元素。因此,在两个版本的《沙滩上的骑手》中的第二个版本中,云雾缭绕和泡沫破浪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而两个远处的灰马人物则与其他象征死亡的画作中的相似人物相呼应。
高更此时选择画风景、静物和人物研究,着眼于沃拉德的客户,避免他的塔希提岛绘画中原始和失落的天堂主题。但是上一时期的三张重要作品表明了更深层次的担忧。其中前两个是《有扇子的女孩》和 《戴红披风的马克萨斯人》。 年轻女子的模特是红头发的托霍陶瓦(Tohotaua),她是邻近岛屿上一位酋长的女儿。男巫师的模特可能是 哈普阿尼(Haapuani),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舞者,也是一位令人畏惧的魔术师,他是高更的密友,据丹尼尔森(Danielsson) 说,他娶了托霍陶瓦(Tohotau)。托霍陶瓦裙子的白色是波利尼西亚文化中权力和死亡的象征,这位模特为整个濒临灭绝的毛希文化尽责。 第二幅似乎是在同一时间绘制的,描绘了一个穿着异国情调的红色斗篷的长发年轻人。该图像的雌雄同体性质引起了批评,人们猜测高更打算描绘摩诃(māhū,即第三性别的人)。三人组的第三张照片是神秘而美丽的《野蛮人的故事》在右边再次出现了托霍陶瓦(Tohotau)。左边的人物是梅耶·德·哈恩,他是高更在阿文桥时代的画家朋友,几年前去世。而中间的人物又是雌雄同体,佛陀般的姿势和莲花暗示,这幅画是对生命永恒循环和重生可能性的沉思。当这些画作在高更突然去世后到达沃拉德时,人们对高更绘制这些画的意图一无所知。
1902年3月,法属波利尼西亚总督爱德华·佩蒂特( Édouard Petit)抵达马克萨斯进行视察。他由爱德华·查理尔( Édouard Charlier) 陪同担任司法系统的负责人。查理尔是一位业余画家,1895 年他第一次来到帕皮提担任地方法官时,就与高更成为了朋友。然而,当查理尔拒绝起诉高更当时的瓦赫尼·波乌拉犯下的一些琐碎罪行时,他们的关系变成了敌意,据称是入室盗窃和盗窃,当高更不在帕皮提工作时,她在普纳奥亚犯了罪。高更甚至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攻击查理尔关于黄蜂( Les Guêpes) 事件。佩蒂特,大概是适当地预先警告过,拒绝看到高更表达定居者对令人反感的税收制度的抗议(高更是他们的发言人),其中大部分收入来自马克萨斯在帕皮提。高更在 4 月做出回应,拒绝缴纳税款,并鼓励定居者、商人和种植者也这样做。
大约在同一时间,高更的健康再次开始恶化,再次出现同样熟悉的一系列症状,包括腿痛、心悸和全身虚弱。他受伤的脚踝疼痛难以忍受,7 月,他不得不从帕皮提订购一个马车,以便他可以在镇上四处走动。到了 9 月,疼痛非常严重,以至于他不得不注射吗啡。他的视力也开始衰退,正如他在最后一张已知自画像中戴的眼镜所证明的那样。这实际上是他的朋友阮文锦(Ky Dong)自己开始的一幅肖像,他自己完成了,因此它的风格与众不同。它显示了一个人疲惫和衰老,但还没有完全被打败。有一段时间他考虑回到欧洲,去西班牙接受治疗。蒙弗雷德劝告他:
在返回时,您将冒着破坏公众对您的赞赏的孵化过程的风险。目前,您是一位独特而传奇的艺术家,从遥远的南海向我们发送令人不安和无法模仿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一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伟人的最终创作。你的敌人——就像那些让平庸感到不安的人一样,你有很多敌人——沉默。但他们不敢攻击你,想都别想。你离得那么远。你不应该回来……你已经和所有伟大的死者一样无懈可击,你已经属于艺术史了。
— 乔治·丹尼尔·蒙弗雷德,1902 年 10 月左右写给保罗·高更的信
1902 年 7 月,怀有七个月身孕的瓦奥霍(Vaeoho) 离开高更回到她邻近的 山谷,与家人和朋友一起生孩子。她在九月份生了孩子,但没有回来。高更随后没有再接再厉。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与马丁主教关于传教士学校的争吵达到了顶峰。当地宪兵德西雷·夏皮耶 (Désiré Charpillet) 起初对高更友好,他向居住在邻近努库希瓦岛的岛群管理员写了一份报告,批评高更鼓励当地人让孩子辍学并鼓励定居者扣留他们的税款。幸运的是,行政长官的职位最近由高更的老朋友弗朗索瓦·皮克诺 (François Picquenot) 担任,他是来自塔希提岛的高更 (Gauguin) 的老朋友,基本上对他表示同情。皮克诺建议夏皮耶不要对学校问题采取任何行动,因为高更有法律支持他,但授权夏皮耶从高更没收货物以代替缴纳税款,如果一切都失败了。可能是由于孤独,有时无法绘画,高更开始写作。
同年 5 月 27 日,南十字星(Croix du Sud) 号轮船在阿帕塔基环礁附近遭遇海难,该岛有三个月没有邮件或补给。邮件服务恢复后,高更在一封公开信中对珀蒂州长进行了愤怒的攻击,抱怨他们在海难后被遗弃的方式。这封信是由《黄蜂》(Les Guêpes) 的继任报纸《独立》(L'Indepéndant ) 于同年 11 月在帕皮提出版的。事实上,佩蒂特奉行了独立和支持本土的政策,令罗马天主教党感到失望,报纸正准备对他进行攻击。高更还将这封信寄给了法兰西美居酒店,后者在他死后出版了一份经过编辑的版本。随后,他给帕皮提宪兵队的负责人写了一封私信,抱怨他当地的宪兵夏皮勒过度强迫囚犯为他劳作。 虽然这些和类似的抱怨是有根据的,但它们的动机都是虚荣心和单纯的仇恨。碰巧的是,那年 12 月,相对支持的夏皮耶被另一名来自塔希提岛的宪兵让 - 保罗·克拉弗里 (Jean-Paul Claverie) 所取代,他对高更的态度远不如前任。
12 月,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几乎无法绘画。他开始撰写自传体回忆录,他称之为 《之前和之后》(Avant et après),并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完成。这个标题应该反映他来塔希提岛前后的经历,并向他自己的祖母未出版的回忆录过去和未来致敬。事实证明,他的回忆录是对波利尼西亚生活、他自己的生活以及对文学和绘画的评论的零散观察集。他在其中包括对当地宪兵、马丁主教、他的妻子梅特和丹麦人等各种不同主题的攻击,并在总结中描述了他的个人哲学,他认为生活是一场存在主义斗争,以调和对立的二元论。马修斯指出两个结束语是对他哲学的提炼:
没有人是好的,没有人是邪恶的,每个人都是两者,以相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方式。 …
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人的生命,但仍有时间做伟大的事情,共同任务的碎片。
— 保罗·高更,《私密日记》,1903 年
他将手稿寄给方丹纳斯进行编辑,但在高更死后版权归梅特所有,直到 1918 年才出版(传真版); 1921 年出现的美国译本。
死亡
1903 年初,高更发起了一场运动,旨在揭露岛上宪兵的无能,尤其是让-保罗·克拉维里 (Jean-Paul Claverie) 在涉及一群人涉嫌酗酒的案件中直接站在当地人一边。然而,克拉维里逃脱了谴责。 2 月初,高更写信给行政长官弗朗索瓦·皮克诺 (François Picquenot),指控克拉维里 (Claverie) 的一名下属腐败。 皮克诺调查了这些指控,但无法证实这些指控。克拉维里的回应是对高更提出诽谤宪兵的指控。随后,他于 1903 年 3 月 27 日被当地地方法官处以 500 法郎的罚款和三个月的监禁。高更立即提出上诉,并着手筹集资金前往帕皮提听取他的上诉。
此时高更身体虚弱,痛苦万分,再次使用吗啡。他于 1903 年 5 月 8 日早上突然去世。
早些时候,他派他的牧师保罗·维尼尔 (Paul Vernier) 来,抱怨他晕倒了。他们一起聊了聊,相信他的情况已经稳定了。然而,高更的邻居蒂奥卡在 11 点钟发现他死了,通过咀嚼他的头试图让他复活,以传统的马克桑方式证实了这一事实。在他的床边放着一瓶空的劳丹脂,这让人猜测他是服药过量的受害者。有人认为他死于心脏病发作。
直到 1903 年 8 月 23 日,高更去世的消息才传到法国。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他的价值较低的遗产在阿图纳拍卖,而他的信件、手稿和绘画于 1903 年 9 月 5 日在帕皮提拍卖。马修斯注意到他的影响的这种迅速传播导致了关于他晚年的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的丢失。汤姆森指出,他的作品拍卖清单(其中一些被当作色情作品烧毁)揭示了他的生活并不像他喜欢的那样贫穷或原始。梅特·高更(Mette Gauguin)适时收到了拍卖所得,约 4,000 法郎。在帕皮提拍卖的其中一幅画作是《母性(二)》,它是 埃尔米塔日博物馆(Hermitage) 中《母性I》(Maternité I ) 的缩小版。原作是在他当时他们的儿子埃米尔(Emile) 降生时绘制的。不知道他为什么画了较小的副本。这幅画以 150 法郎的价格卖给了法国海军军官科钦司令,他说佩蒂特州长本人为这幅画出价高达 135 法郎。它于 2004 年在苏富比以 39,208,000 美元的价格售出。
2014 年,法医对高更家附近一口井的玻璃罐中发现的四颗牙齿进行了法医检查,对高更患有梅毒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 DNA 检查确定这些牙齿几乎可以肯定是高更的牙齿,但没有发现当时用于治疗梅毒的汞的痕迹,这表明高更没有患有梅毒,或者他没有接受治疗。 2007 年,考古学家在高更在马奎斯群岛的希瓦奥岛建造的一口井底部发现了四颗可能是高更的腐烂臼齿。
历史意义
原始主义是 19 世纪后期绘画和雕塑的艺术运动,其特点是夸张的身体比例、动物图腾、几何图案和鲜明的对比。第一位系统地使用这些效果并在公众中取得广泛成功的艺术家是保罗·高更。欧洲文化精英第一次发现非洲、密克罗尼西亚和美洲原住民的艺术,被这些遥远地方的艺术所体现的新奇、狂野和鲜明的力量所吸引、着迷和教育。就像 20 世纪初的巴勃罗·毕加索一样,高更的灵感和动力来自那些外国文化所谓的原始艺术的原始力量和简单性。
高更也被认为是后印象派画家。他大胆、色彩丰富且以设计为导向的绘画对现代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20 世纪早期受他启发的艺术家和运动包括文森特·梵高、亨利·马蒂斯、巴勃罗·毕加索、乔治·布拉克、安德烈·德兰、野兽派、立体主义和奥菲斯主义等。后来,他影响了亚瑟·弗兰克·马修斯和美国工艺美术运动。
约翰·雷瓦尔德 (John Rewald) 被公认为 19 世纪后期艺术领域的权威,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后印象派画家的书籍时期,包括后印象派:从梵高到高更(1956 年)和一篇文章,保罗·高更:给安布罗斯·沃拉德和安德烈·丰泰纳斯的信(收录于雷瓦尔德的后印象派研究,1986 年),讨论了高更在塔希提岛的岁月和斗争通过与艺术品经销商沃拉德和其他人的通信可以看出他的生存情况。
对毕加索的影响
高更于 1903 年在巴黎秋季沙龙举办的死后回顾展,以及 1906 年更大的回顾展,对法国先锋派,尤其是巴勃罗·毕加索的画作产生了惊人而强大的影响。 1906 年秋天,毕加索创作了超大的裸体女性和不朽的雕塑人物画,让人想起保罗·高更的作品,表现出他对原始艺术的兴趣。毕加索 1906 年的巨幅人物画直接受到高更雕塑、绘画和写作的影响。高更作品所唤起的力量直接导致了 1907 年的 《亚维农少女》。
根据高更传记作者大卫·斯威特曼的说法,毕加索早在 1902 年就在巴黎遇到了西班牙侨民雕塑家兼陶艺家帕科·杜里奥,并成为了高更作品的粉丝。杜里奥手头有几幅高更的作品,因为他是高更的朋友,也是他作品的无偿代理人。杜里奥试图通过在巴黎宣传他的作品来帮助他在大溪地贫困的朋友。在他们见面后,杜里奥向毕加索介绍了高更的粗陶器,帮助毕加索制作了一些陶瓷作品,并给了毕加索第一版《诺亚诺亚:保罗·高更的塔希提岛杂志》。除了在杜里奥那里看到高更的作品,毕加索还在安布罗斯·沃拉德 (Ambroise Vollard )的画廊看到了他和高更的作品。
关于高更对毕加索的影响,约翰·理查森写道:
1906 年的高更作品展让毕加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这位艺术家的束缚。高更展示了最不同类型的艺术——更不用说来自形而上学、民族学、象征主义、圣经、古典神话等等的元素——可以组合成一个既符合时代又永恒的综合体。他证明,一位艺术家还可以通过将他的恶魔驾驭黑暗之神(不一定是大溪地的)并挖掘新的神圣能量来源来混淆传统的美感。如果在晚年毕加索淡化了对高更的亏欠,毫无疑问,在 1905 年至 1907 年间,他与另一位保罗有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后者以从秘鲁祖母那里继承的西班牙基因而自豪。毕加索没有以高更的名义签下自己的“保罗”。
根据理查森的说法,
毕加索在 1906 年秋季沙龙高更回顾展上看到的例子进一步激发了毕加索对粗陶器的兴趣。这些陶瓷中最令人不安的(毕加索可能已经在沃拉德看到过)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奥维里。直到 1987 年,奥赛博物馆收购了这件鲜为人知的作品(自 1906 年以来只展出过一次),它才被公认为是杰作,更不用说因为它与导致少女时代的作品的相关性而被公认为的。虽然只有不到 30 英寸高,但奥维里却有着令人敬畏的存在,就像一座为高更坟墓设计的纪念碑。毕加索对奥维里的印象非常深刻。 50 年后,当库珀和我告诉他我们在一个收藏品中看到了这尊雕塑时,他很高兴,其中还包括他的立体派头部的原始石膏。它是一种启示,就像伊比利亚雕塑一样吗?毕加索耸了耸肩,勉强表示肯定。他总是不愿意承认高更在让他走上原始主义道路上的作用。
技术和风格
高更最初的艺术指导来自毕沙罗,但这种关系留下的印象更多是个人而非风格。高更的大师是乔托、拉斐尔、安格尔、欧仁德拉克洛瓦、马奈、德加和塞尚。他自己的信仰,在某些情况下,他作品背后的心理学也受到哲学家亚瑟·叔本华和诗人斯蒂芬·马拉美的影响。
高更,就像他同时代的一些人一样埃德加·德加和图卢兹·罗特列克,采用了一种在画布上绘画的技术,称为汽油喷漆。为此,油从油漆中排出,剩余的颜料淤泥与松节油混合。他可能使用了类似的技术来准备他的单字,使用纸而不是金属,因为它会吸收油,使最终图像具有他想要的哑光外观。他还在玻璃的帮助下校对了他现有的一些图纸,用水彩或水粉将下面的图像复制到玻璃表面上进行印刷。高更的木刻作品同样具有创新性,即使对于当时负责木刻复兴的前卫艺术家来说也是如此。高更最初不是为了制作详细的插图而切割他的块,而是以类似于木雕的方式雕刻他的块,然后使用更精细的工具在他大胆的轮廓中创造细节和色调。他的许多工具和技术都被认为是实验性的。这种方法和空间的使用与他的平面装饰性浮雕画平行。
从马提尼克岛开始,高更开始在附近使用类似的颜色来实现柔和的效果。此后不久,他也在非具象色彩上取得突破,创作出具有独立存在和生命力的画布。表面现实和他自己之间的这种差距使毕沙罗不高兴,并迅速导致他们的关系结束。他此时的人物形象也提醒着他对日本版画的热爱,尤其是他们人物的天真和构图的朴素对他原始宣言的影响。正因为如此,高更也受到了民间艺术的启发。他寻求以直截了当的方式传达的主题的纯粹情感,强调主要形式和直立的线条以明确定义形状和轮廓。高更还在抽象的图案中使用了精致的正式装饰和色彩,试图协调人与自然。他对自然环境中的原住民的描绘经常表现出宁静和自给自足的可持续性。这赞美了高更最喜欢的主题之一,即超自然现象对日常生活的侵入。
在 1895 年 3 月 15 日出版的《巴黎之声》的采访中,高更解释说,他不断发展的战术方法是达到联觉。他说:
我画中的每一个特征都是事先经过仔细考虑和计算的。就像在音乐作品中一样,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从日常生活或自然中取材的简单对象只是一个借口,它通过一定的线条和颜色的排列来帮助我创造交响乐和和声。他们在现实中根本没有对应物,在那个词的粗俗意义上;它们不直接表达任何想法,它们的唯一目的是激发想象力——就像音乐不需要想法或图片的帮助一样——仅仅通过颜色和线条的某些安排与我们的思想之间存在的神秘亲和力。
在 1888 年给埃米尔·舒芬尼克的一封信中,高更解释了他从印象派迈出的巨大一步,他现在致力于捕捉大自然的灵魂、古老的真理以及风景和居民的特征。高更写道:
不要从字面上复制自然。艺术是一种抽象。当你在大自然面前做梦时,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更多地考虑创造的行为而不是结果。
遗产
高更的作品在他死后不久就开始流行起来。他后来的许多画作都被俄罗斯收藏家谢尔盖·舒金 (Sergei Shchukin) 收购。他的大部分藏品都陈列在普希金博物馆和冬宫。高更画作极少挂牌,上架时在售楼处售价高达数千万美元。他的 1892 年《什么时候嫁人?》成为世界上第三贵的艺术品,当时它的主人 鲁道夫·斯塔赫林(Rudolf Staechelin )家族于 2014 年 9 月以 2.1 亿美元的价格私下将其出售。据信买家是卡塔尔博物馆.
高更的生活启发了萨默塞特·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Mario Vargas Llosa) 以他 2003 年的小说《达标之路》(The Way to Par) 为基础关于高更的生活,以及他的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的生活。
演员安东尼·奎因在 1956 年梵高传记片《欲望人生》中饰演高更,并因其表演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奥斯卡·艾萨克在后来的梵高传记片《永恒之门》中饰演高更。弗拉基米尔·约达诺夫在 1990 年的电影《文森特与提奥》中饰演高更。
日式风格的高更博物馆位于塔希提岛帕皮里的帕皮里植物园对面,收藏有高更和大溪地人的一些展品、文件、照片、复制品以及原始草图和版画。 2003 年,保罗·高更文化中心在马克萨斯群岛的阿图纳开业。
2014 年,在意大利发现了 1970 年在伦敦失窃的画作《桌上的水果》(1889 年),估价在 1000 万至 3000 万欧元(830 万至 2480 万英镑)之间。这幅画连同皮埃尔·博纳尔 (Pierre Bonnard) 的作品于 1975 年由一名菲亚特员工在铁路失物招领中以 45,000 里拉(约合 32 英镑)的价格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