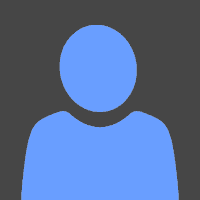卡斯帕·弗里德里希
Caspar David Friedrich
代表作品:
艺术家名:卡斯帕·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
生卒日期: 1774年9月5日 - 1840年5月7日
国籍:德国
卡斯帕·弗里德里希的全部作品(192)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是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通常被认为是他这一代最重要的德国艺术家。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中期寓言式风景画,典型的特点是在夜空、晨雾、贫瘠的树木或哥特式废墟的衬托下描绘出沉思的人物轮廓。他的主要兴趣是对自然的沉思,他的作品通常是象征性的,反古典的,旨在传达对自然世界的主观的、情感的反应。弗里德里希的绘画典型地在广阔的风景中以缩小的视角设置了人类的存在,根据艺术史学家克里斯托弗·约翰·默里的说法,将人物缩小到一个“观众的目光指向他们的形而上学维度”的尺度。
弗里德里希出生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格雷夫斯瓦尔德镇(Greifswald),当时是瑞典波美拉尼亚(Swedish Pomerania)。他在哥本哈根学习到1798年,然后定居在德累斯顿。他成年的时候,整个欧洲对物质主义社会的幻想日益破灭,对精神的新欣赏也随之兴起。这种观念的转变常常通过对自然世界的重新评估来表达,因为弗里德里希、特纳和约翰·康斯特勃等艺术家试图将自然描绘成一种“与人类文明的诡计对立的神圣创造物”。
弗里德里希的作品在他早期的职业生涯中就为他带来了声誉,法国雕塑家大卫·丹格斯(David d'Angers)等同时代人都说他是一个发现了“景观悲剧”的人。然而,他的作品在晚年失宠,默默无闻地死去。随着德国在19世纪末走向现代化,一种新的紧迫感成为其艺术的特征,弗里德里希对静谧的沉思式描绘被视为过去时代的产物。20世纪初,他的作品再次受到人们的赞赏,从1906年开始,他在柏林举办了32幅画展。到了20世纪20年代,他的绘画被表现主义者发现,在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超现实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经常从他的作品中汲取灵感。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主义的兴起再次见证了弗里德里希受欢迎程度的回升,但随后他的画作由于与纳粹运动的联系而被解读为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因此其受欢迎程度急剧下降。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弗里德里希才重新获得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标志和国际重要画家的声誉。
生活
早年与家庭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于1774年9月5日出生于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瑞典波美拉尼亚格雷夫斯瓦尔德。他是十个孩子中的第六个,在父亲阿道夫·戈特利布·弗里德里希(Adolf Gottlieb Friedrich)的严格信条下长大,父亲是蜡烛制造者和肥皂制造者。家庭财务状况的记录相互矛盾;虽然一些消息来源表明这些孩子是在私人辅导下长大的,但另一些消息来源记录说,他们是在相对贫困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从小就熟悉死亡。他的母亲索菲于1781年去世,当时他七岁。一年后,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去世,另一个妹妹玛丽亚于1791年死于斑疹伤寒。可以说,他童年最大的悲剧发生在1787年,当时他的兄弟约翰·克里斯托夫去世:13岁时,卡斯帕·大卫目睹他的弟弟从结冰的湖面上摔下,溺水身亡。一些报道表明,约翰·克里斯托夫在试图营救卡斯帕·大卫时丧生,而卡斯帕·大卫也在冰上处于危险之中。
弗里德里希于1790开始了他的正式艺术研究,作为他在家乡格赖夫斯瓦尔德的的艺术家约翰·戈特弗里德·奎斯托普(Johann Gottfried Quistorp)的私人学生,艺术系现在被命名为卡斯帕戴维弗里德里希学院(Caspar-David-Friedrich-Institut)。奎斯托普带着他的学生们去户外画画;因此,弗里德里希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鼓励从生活中写生。通过奎斯托普,弗里德里希结识了神学家路德维希·戈特哈德·科塞加滕( Ludwig Gotthard Kosegarten),并受到其影响,他教导人们自然是上帝的启示。奎斯托普向弗里德里希介绍了17世纪德国艺术家亚当·埃尔斯海默的作品,他的作品通常包括以风景为主的宗教主题和夜间活动主题。在此期间,他还与瑞典教授托马斯·托里尔德(Thomas Thorild)一起学习文学和美学。四年后,弗里德里希进入享有盛名的哥本哈根学院,在那里,他开始接受教育,先复制古董雕塑的模型,然后开始从生活中绘画。住在哥本哈根使这位年轻的画家有机会接触到皇家美术馆收藏的17世纪荷兰风景画。在该学院,他在Christian August Lorentzen和风景画家Jens Juel等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这些艺术家的灵感来源于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运动,代表了新兴浪漫主义美学的戏剧性强度和表达方式与日渐衰落的新古典主义理想之间的中点。情绪是至高无上的,影响来自于诸如冰岛埃达传说( legend of Edda)、莪相(Ossian,爱尔兰英雄吟游诗人)和挪威神话中的诗歌等来源。
搬到德累斯顿
1798年,弗里德里希在德累斯顿永久定居。在这个早期阶段,他尝试版画制作,蚀刻版画和木刻版画的设计都是他哥哥做的。到1804年,他创作了18幅蚀刻画和四幅木刻画;它们显然是少量制作的,只分发给朋友。尽管他涉足其他媒体,但他还是倾向于主要使用墨水、水彩画和乌贼墨。除了一些早期作品,如《废墟中的寺庙风景》( Landscape with Temple in Ruins,1797年),他没有广泛从事油画创作,直到他的名声更加稳固。从1801年开始,他经常去波罗的海海岸、波希米亚、科诺什和哈尔茨山,这激发了他对风景的兴趣。他的绘画大多以德国北部的风景为基础,描绘了森林、山丘、港口、晨雾和其他基于对自然的密切观察的光线效果。这些作品以风景名胜的草图和研究为蓝本,如吕根悬崖、德累斯顿周边地区和易北河。他几乎完全用铅笔进行研究,甚至提供地形信息,但弗里德里希中期绘画中微妙的大气效果特征是凭记忆呈现的。这些效果的力量来自于对光线的描绘,以及太阳和月亮在云层和水面上的照明:波罗的海海岸特有的光学现象,以前从未如此强调过
1805年,他在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组织的魏玛竞赛中获奖,由此确立了他作为艺术家的声誉。当时,魏玛艺术大赛倾向于吸引平庸、现已被遗忘的艺术家,他们呈现出新古典主义和伪希腊风格的衍生混合。作品质量差开始损害歌德的声誉,因此当弗里德里展出两幅作品——《黎明游行》(Procession at Dawn)和《海边渔民》(Fisher-Folk by the Sea)时——诗人热情地回应并写道:“我们必须赞扬艺术家在这幅画中的足智多谋 相当。画得好,行进巧妙得体……他的处理结合了大量的坚定、勤奋和整洁……巧妙的水彩画……也值得称赞。”
弗里德里希在1808年34岁时完成了他的第一幅主要画作。《山中的十字架》是一幅祭坛画板,据说是为波希米亚杰钦(Tetschen)的一个家庭礼拜堂委托制作的。该画板描绘了山顶上的一个十字架,独自一人,四周是松树、 在基督教艺术中,祭坛画首次展示了一幅风景画。据艺术历史学家琳达·西格尔(Linda Siegel)说,弗里德里希的设计是“他早期许多描绘自然界十字架的绘画的逻辑高潮”。"
尽管祭坛画普遍受到冷遇,但这是弗里德里希的第一幅受到广泛宣传的画。艺术家的朋友们公开为这部作品辩护,而艺术评论家巴西利乌斯·冯·拉姆多尔(Basilius von Ramdohr)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质疑弗里德里希在宗教背景下对风景的运用。他拒绝了风景画可以传达明确含义的观点,写道“如果风景画潜入教堂并爬上祭坛,这将是一个真实的假设”。1809年,弗里德里希通过一个节目回应,描述了他的意图,将夕阳的光芒与圣父的光芒进行了比较。这一声明标志着弗里德里希唯一一次记录了对自己作品的详细解读,这幅画是弗里德里希收到的为数不多的委托之一。
在普鲁士王储购买了他的两幅画后,弗里德里希于1810年当选为柏林学院的成员。然而在1816年,他试图与普鲁士当局保持距离,并于6月申请撒克逊国籍。此举出乎意料,撒克逊政府是亲法的,而弗里德里希的画作普遍被视为爱国主义和明显的反法。尽管如此,在他在德累斯顿的朋友格拉夫·维茨敦·冯·埃克斯特(Graf Vitzthum von Eckstädt)的帮助下,弗里德里希获得了公民身份,并于1818年以每年150塔勒的红利成为撒克逊学院的成员。尽管他曾希望获得一个正式的教授职位,但根据德国信息图书馆(German Library of Information)的说法,这一职位从未授予他,因为“人们认为他的绘画过于个人化,他的观点过于个人化,无法成为学生们富有成效的榜样。”政治也可能是阻碍其职业生涯的一个因素:弗里德里希的明显的日耳曼主题和消费经常与当时盛行的亲法态度发生冲突。
结婚
1818年1月21日,弗里德里希与卡罗琳·波默(Caroline Bommer)结婚,卡罗琳·波默是一位来自德累斯顿的染工的25岁女儿。这对夫妇有三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艾玛是1820年出生的。生理学家兼画家卡尔·古斯塔夫·卡鲁斯(Carl Gustav Carus)在他的传记文章中指出,婚姻对弗里德里希的生活或性格都没有重大影响,但他这一时期的油画,包括蜜月后的《吕根岛上的白垩岩》,显示出一种新的轻浮感,而他的调色板则更明亮、更不严肃。在这一时期的绘画中,人物的出现越来越频繁,西格尔将其解释为“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尤其是他的家庭,现在越来越多地占据了他的思想,他的朋友、他的妻子和他的市民成为他艺术中经常出现的主题。”
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在俄罗斯找到了两个来源的支持。1820年,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大公( Grand Duke Nikolai Pavlovich)应其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Alexandra Feodorovna)的要求,参观了弗里德里希的画室,并带回了他的一些画作,这一交换开始了持续多年的赞助。此后不久,亚历山大二世的导师、诗人瓦西里·朱可夫斯基(Vasily Zhukovsky)于1821年与弗里德里希(Friedrich)相遇,并在弗里德里希身上找到了志趣相投的人。几十年来,朱可夫斯基通过亲自购买弗里德里希的作品和向王室推荐他的艺术作品来帮助弗里德里希。在弗里德里希职业生涯结束时,他的帮助对这位身患重病、一贫如洗的艺术家来说是无价的。朱可夫斯基说,他朋友的画“精确地取悦了我们,每一幅都唤起了我们心中的记忆。”
弗里德里希认识Philipp Otto Runge,他是浪漫主义时期另一位德国著名画家。他也是Georg Friedrich Kersting和挪威画家约翰·克里斯蒂安·达尔的朋友,在朴素的画室里为他作画。达尔在艺术家的最后几年与弗里德里希关系密切,他对购买艺术品的公众感到沮丧,因为弗里德里希的画只是“珍品”。诗人朱可夫斯基欣赏弗里德里希的心理主题,达尔赞扬弗里德里希风景画的描述性,并评论说“艺术家和鉴赏家在弗里德里希的艺术中只看到了一种神秘主义,因为他们自己只是在寻找神秘主义者……他们没有看到弗里德里希在他所代表的一切事物中忠实而认真地研究自然”。
在此期间,弗里德里希经常为陵墓绘制纪念性纪念碑和雕塑,反映出他对死亡和来世的痴迷;他甚至还为德累斯顿公墓中的一些葬礼艺术设计。其中一些作品在烧毁慕尼黑玻璃宫(Glass Palace,1931年)的大火中丢失,后来在1945年德累斯顿爆炸案中丢失。
晚年与死亡
在弗里德里希生命的最后15年里,他的声誉稳步下降。随着早期浪漫主义的理想从时尚中消失,他逐渐被视为一个古怪而忧郁的人物,与时代脱节。他的赞助人渐渐地消失了。到1820年,他已经过着隐士的生活,朋友们称他为“孤独中最孤独的人”。他临终时生活相对贫困。他变得孤立无援,日夜长时间独自在树林和田野里散步,常常在日出前开始散步。
1835年6月,弗里德里希第一次中风,导致他四肢瘫痪,大大降低了他的绘画能力。因此,他无法进行油画工作;取而代之的是,他仅限于水彩画、乌贼墨画和对旧作品的重新创作。
虽然他的视力仍然很强,但他已经失去了手的全部力量。然而,他最终创作了一幅《月光下的海岸》,被沃恩(Vaughan)描述为“他所有海岸线中最黑暗的一幅,其中丰富的色调弥补了他以前技巧的不足”。
死亡的象征出现在他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中。在他中风后不久,俄罗斯皇室购买了他早期的一些作品,这些收益使他得以前往今天捷克共和国的泰普利茨( Teplitz)恢复健康。
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弗里德里希开始了一系列的肖像画,他又回到了观察大自然中的自己。然而,正如艺术史学家威廉·沃恩(William Vaughan)所观察到的那样,“他可以将自己视为一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人。他不再是1819年《凝月(新大师画廊藏)》中出现的那种正直、支持的人物。他又老又僵硬……他弯腰走路。”。
到1838年,他只能绘制小规模作品。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越来越依赖朋友的帮助慈善。
弗里德里希于1840年5月7日在德累斯顿去世,葬在市中心以东的德累斯顿三一公墓(Trinitatis-Friedhof,Trinity Cemetery,大约15年前他曾画过的入口)。这座简朴平坦的墓碑位于主大道内中央圆形建筑的西北方向。
到他去世时,他的声誉和名望都在下降,他的去世在艺术界几乎没有引起注意。他的作品在他有生之年肯定得到了认可,但并不广泛。虽然在当代艺术中,对风景的仔细研究和对自然精神要素的强调是司空见惯的,但他的作品过于独创和个人化,难以被充分理解。到1838年,他的作品不再畅销,也不再受到评论家的关注,浪漫主义运动已经远离了艺术家帮助建立的早期理想主义。
卡尔·古斯塔夫·卡鲁斯在他死后写了一系列文章,赞扬弗里德里希对风景画传统的转变。然而,卡鲁斯的文章坚定地将弗里德里希置于他那个时代,并没有将这位艺术家置于一个持续的传统之中。他的画作中只有一幅被复制成印刷品,而且复制品很少。
主题
景观与崇高
新的风景画家在自然界中看到的100度的视野,他们无情地挤在一起,形成一个只有45度的视角。此外,自然界中被大空间隔开的东西,被压缩成一个狭窄的空间,使眼睛过度充盈和满足,对观看者造成不利和令人不安的影响。
—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
以全新的方式对景观进行可视化和描绘是弗里德里希的关键创新。他不仅像经典观念中那样探索美丽景色的极乐享受,而且还通过对自然的沉思来审视崇高的瞬间,与精神自我的重聚。弗里德里希有助于将艺术中的风景从人类戏剧的背景转变为独立的情感主题。弗里德里希的画作通常使用背后视角( Rückenfigur)——一个从背后观察风景的人。观众被鼓励将自己置于人物后端的位置,通过这种方式,他体验到大自然的崇高潜力,理解到场景是由人类感知和理想化的。弗里德里希创造了一个充满浪漫情怀的景观概念。他的艺术描绘了广泛的地理特征,如岩石海岸、森林和山景。他经常用风景来表达宗教主题。在他那个时代,大多数最著名的绘画都被视为宗教神秘主义的表现。
弗里德里希说:“艺术家不仅应该画他眼前看到的东西,还应该画他内心看到的东西。但是,如果他什么也看不到,那么他也应该避免画他眼前看到的东西。否则,他的画将像那些折叠式屏风,人们期望在它后面只能看到病人或死者。”广阔的天空、风暴、薄雾、森林、废墟和十字架见证了上帝的存在,这些都是弗里德里希风景中常见的元素。虽然死亡在远离海岸的船只上有象征性的表达——一种像卡戎(Charon)一样的图案,在白杨树上也有,但在《橡树下的寺院》等画作中,死亡更直接地被提及。在这些画作中,僧侣们抬着棺材穿过一座敞开的坟墓,走向十字架,穿过一座废墟教堂的大门。
他是第一批描绘冬季风景的艺术家之一,在这些风景中,土地被渲染成了死气沉沉的样子。弗里德里希的冬季场景是庄严的,根据艺术历史学家赫尔曼·比恩肯(Hermann Beenken)的说法,弗里德里希画的冬季场景中“还没有人站稳脚跟。几乎所有较老的冬季图片的主题都不是冬天本身,而是冬天的生活。在16和17世纪,人们认为不可能忽略诸如滑冰者人群、流浪者……正是弗里德里希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然生命的完全超然和独特的特征。他寻找的不是许多音调,而是一种音调;因此,在他的风景画中,他把合成和弦放在一个单一的基本音符中”。
光秃秃的橡树和树桩,如《乌鸦树》、《凝月(国家美术馆藏)》和《夕阳下的柳树丛》(Willow Bush under a Setting Sun ),是弗里德里希绘画中反复出现的元素,象征着死亡。与绝望相对应的是弗里德里希救赎的象征:十字架和晴朗的天空预示着永生,细长的月亮暗示着希望和基督越来越亲近。在他的海洋绘画中,锚经常出现在岸边,也表明了一种爱精神上的希望。德国文学学者艾丽斯·库兹尼亚尔(Alice Kuzniar)在弗里德里希的绘画中发现了一种时间性,一种在视觉艺术中很少被强调的对时间流逝的唤起。例如,在奥克伍德的修道院,僧侣们离开敞开的坟墓,走向十字架和地平线的运动传递了弗里德里希的信息,即人类生命的最终目的地在坟墓之外。
黎明和黄昏构成了他风景画的突出主题,弗里德里希晚年的特点是日益悲观。他的作品变得更加黑暗,显示出一种可怕的纪念性。《冰之海》——也许是对弗里德里希在这一点上的思想和目标的最好概括,尽管以一种激进的方式,这幅画并不受欢迎。它完成于1824年,描绘了一个严峻的主题,北冰洋的一次海难。“他制作的图像,用石灰华颜色的浮冰磨碎了一艘木船,超越了纪录片,变成了寓言:人类渴望的脆弱树皮被世界巨大的冰川冷漠所粉碎。”
弗里德里希对美学的书面评论仅限于1830年制定的一套格言,其中他解释了艺术家需要将自然观察与对自己个性的内省审视相匹配。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建议艺术家“闭上你的肉体之眼,这样你就可以先用精神之眼看到你的画,然后把你在黑暗中看到的东西带到白昼的光中,这样它就可以从外面到里面对别人作出反应。”他拒绝在“整体性”中过度描绘自然,正如Ludwig Richter和约瑟夫·安东·科赫等当代画家的作品中所发现的那样。
孤独与死亡
弗里德里希的生活和艺术有时被一些人认为带有一种压倒性的孤独感。艺术史学家和一些与他同时代的人将这种解释归因于他年轻时所遭受的损失,归因于他成年后的暗淡前景,而弗里德里希苍白而孤僻的外表有助于强化“来自北方的沉默寡言的人”的流行观念。
弗里德里希在1799年、1803年至1805年、约1813年、1816年以及1824年至1826年间经历了抑郁发作。在这些插曲中,他创作的作品出现了明显的主题变化,出现了秃鹫、猫头鹰、墓地和废墟等主题和符号。从1826年起,这些图案成为他作品的永久特征,而他对颜色的使用变得更加黑暗和柔和。卡鲁斯在1929年写道,弗里德里希“被精神上的不确定性所笼罩”,尽管著名艺术史学家和策展人休伯特斯·加斯纳(Hubertus Gassner)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弗里德里希的作品中有一种积极的、肯定生命的潜台词,其灵感来自共济会和宗教。
日耳曼民俗
1813年法国占领波美拉尼亚期间,弗里德里希的爱国主义和怨恨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来自德国民间传说的主题越来越突出。弗里德里希是一位反法的德国民族主义者,他用自己家乡的风景画来庆祝日耳曼文化、习俗和神话。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和西奥多·科尔纳(Theodor Körner)的反拿破仑诗歌以及亚当·穆勒(Adam Müller)和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爱国主义文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弗里德里希被三位朋友在与法国的战争中丧生以及克莱斯特(Kleist)1808年的戏剧《赫尔曼战役》(Die Hermannsschlacht)所感动,他创作了一系列绘画作品,试图仅通过风景来传达政治象征——这在艺术史上尚属首次。
在《为独立而战的阵亡将士陵墓》中,一座刻有“阿米纽斯”(Arminius)字样的破旧纪念碑唤起了民族主义的象征——日耳曼酋长,而四座倒下英雄的陵墓略微半开着,让他们的灵魂永远自由。两名法国士兵以小人物的身份出现在一个洞穴前,洞穴较低且较深,四周环绕着岩石,似乎离天堂更远。第二幅政治画作《森林中的猎人》描绘了一位迷路的法国士兵,被茂密的森林衬托得矮小,而树桩上栖息着一只乌鸦——一位末日预言家,象征着法国的预期失败。
遗产
影响
与其他浪漫主义画家一起,弗里德里希帮助将风景画定位为西方艺术的主要流派。在他的同时代人中,弗里德里希的风格对约翰·克里斯蒂安·达尔的绘画影响最大。在后来的几代人中,阿诺德·伯克林深受其作品的影响,而弗里德里希的作品大量出现在俄罗斯收藏品中影响了许多俄罗斯画家,特别是阿基普·奎因芝和伊万·希什金。弗里德里希的精神期待着美国画家,如艾伯特·平克汉姆·莱德、拉尔夫·阿尔伯特·布莱克洛克、哈德逊河学派和新英格兰发光派画家。
20世纪之交,挪威艺术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奥伯特( Andreas Aubert ,1851-1913)重新发现了弗里德里希,他的作品开创了现代弗里德里希学术,象征主义画家也重新发现了弗里德里希,他们珍视他的幻想和寓言风景。挪威象征主义者爱德华·蒙克在19世纪80年代访问柏林时可能会看到弗里德里希的作品。蒙克1899年的印刷品《两个人,孤独的人》与弗里德里希的《云海之上的徒步者》相呼应,尽管在芒克的作品中,重点已经从广阔的风景转向前景中两个忧郁人物之间的错位感。
弗里德里希的现代复兴在1906年获得了动力,当时他的32幅作品在柏林的浪漫主义时期艺术展上展出。他的风景画对德国艺术家马克斯·恩斯特的作品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其他超现实主义者开始将弗里德里希视为他们运动的先驱。1934年,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在他的作品《人类状况》中表达了敬意,这部作品直接呼应了弗里德里希艺术中对感知和观众角色的质疑。几年后,超现实主义杂志《米诺陶》(Minotaure)在1939年由评论家玛丽·兰茨伯格(Marie Landsberger)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弗里德里希,从而将他的作品展示给了更广泛的艺术家圈。恩斯特的狂热崇拜者保罗·纳什在1940-1941年间的作品《死海》中,就可以明显看出《冰之海》的影响。弗里德里希的作品被其他20世纪的主要艺术家引用为灵感来源,包括马克·罗斯科、格哈德·里希特、哥达德·格拉布纳(Gotthard Graubner)和安塞姆·基弗。弗里德里希的浪漫主义绘画也被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89)挑了出来,他站在《凝月(国家美术馆藏)》面前说:“你知道,这是《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的源泉。”
艺术史学家罗伯特·罗森布鲁姆(Robert Rosenblum)在其1961年发表的文章《抽象崇高》(The Abstract Sublime)中,将弗里德里希和特纳的浪漫主义风景画与马克·罗斯科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进行了比较。罗森布卢姆特别描述了弗里德里希1809年的《海边的僧侣》、特纳的《夜星》(The Evening Star)和罗斯科1954年的《光、大地和蓝色》(Light, Earth and Blue),这些作品揭示了视觉和情感的密切关系。据罗森布鲁姆说,罗斯科,像弗里德里希和特纳一样,把我们置于崇高美学家所讨论的那些无形的无限的门槛上。弗里德里希作品中的和尚和特纳作品中的费舍尔在泛神论上帝的无限浩瀚和他的生物的无限渺小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罗斯科的抽象语言中,这样的文字细节——真正的观众和先验景观呈现之间的移情桥梁——已不再必要。我们自己就是海前的和尚,静静地、沉思地站在这些巨大而无声的画面前,仿佛我们在看日落或月夜。"
当代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普尔(Christiane Pooley)从弗里德里希(Friedrich)的作品中获得灵感,她的风景画重新诠释了智利的历史。
批评意见
直到1890年,尤其是在他的朋友去世后,弗里德里希的作品几乎被遗忘了几十年。然而,到了1890年,他的作品中的象征意义开始与当时的艺术氛围相吻合,尤其是在中欧。然而,尽管人们对他的独创性重新产生了兴趣,并承认了他的独创性,但他对“绘画效果”的缺乏关注而且渲染得很薄的表面与当时的理论格格不入。
当时代的要求与我的信念背道而驰时,我不会软弱到屈服于时代的要求。我在自己周围织了一个茧,让其他人也这样做。我将把它留给时间来展示它将带来什么:一只灿烂的蝴蝶或蛆。
—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
20世纪30年代,弗里德里希的作品被用于宣传纳粹意识形态,试图将这位浪漫主义艺术家融入民族主义的血与土(Blut und Boden)。弗里德里希的声誉花了几十年才从与纳粹主义的联系中恢复过来。他对象征主义的依赖以及他的作品不属于现代主义狭义定义的事实导致了他的失宠。1949年,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写道,弗里德里希“以他那个时代的冰冷技术工作,这很难激发现代绘画流派的灵感”,并暗示艺术家试图在绘画中表达最好留给诗歌的东西。克拉克对弗里德里希的辞退反映了这位艺术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声誉受到的损害。
弗里德里希的形象被一些好莱坞导演采用,比如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这进一步损害了弗里德里希的声誉。他的形象是建立在弗里茨·朗(Fritz Lang)和F.W.穆诺(Friedrich Wilhelm Murnau)等德国电影大师的恐怖和幻想类型作品的基础上的。他声誉的康复是缓慢的,但通过沃纳·霍夫曼(Werner Hofmann)、赫尔穆特·贝尔什·苏潘(Helmut Börsch-Supan)和西格丽德·辛茨(Sigrid Hinz)等批评家和学者的著作,他的恢复得到了加强,他们成功地拒绝和反驳了归因于他的作品的政治联想,并将其置于纯粹的艺术历史背景中。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再次在世界各地的主要画廊展出,因为他受到了新一代评论家和艺术史学家的青睐。
今天,他的国际声誉已经确立。他是祖国德国的民族偶像,受到西方世界艺术史学家和艺术鉴赏家的高度评价。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心理复杂的人物,沃恩认为,一个与怀疑作斗争的信徒,一个被黑暗困扰的美丽的庆祝者。最终,他超越了诠释,通过其形象的引人注目的吸引力跨越了文化。他真的变成了一只蝴蝶,希望它永远不会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
作品
弗里德里希是一位多产的艺术家,创作了500多件作品。与他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理想相一致,他打算让他的绘画成为纯粹的审美陈述,因此他谨慎地认为,他的作品的标题不太具有描述性或唤起性。很可能,今天一些更具文字色彩的标题,如《生命阶段》,并非由艺术家本人给出,而是在弗里德里希的一次兴趣复兴中采用的。约会弗里德里希的作品时会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部分原因是他经常不直接给自己的画布命名或注明日期。然而,他在自己的作品上保留了一个详细的笔记本,学者们用它来将绘画与完成日期联系起来。
生卒日期: 1774年9月5日 - 1840年5月7日
国籍:德国
卡斯帕·弗里德里希的全部作品(192)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是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通常被认为是他这一代最重要的德国艺术家。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中期寓言式风景画,典型的特点是在夜空、晨雾、贫瘠的树木或哥特式废墟的衬托下描绘出沉思的人物轮廓。他的主要兴趣是对自然的沉思,他的作品通常是象征性的,反古典的,旨在传达对自然世界的主观的、情感的反应。弗里德里希的绘画典型地在广阔的风景中以缩小的视角设置了人类的存在,根据艺术史学家克里斯托弗·约翰·默里的说法,将人物缩小到一个“观众的目光指向他们的形而上学维度”的尺度。
弗里德里希出生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格雷夫斯瓦尔德镇(Greifswald),当时是瑞典波美拉尼亚(Swedish Pomerania)。他在哥本哈根学习到1798年,然后定居在德累斯顿。他成年的时候,整个欧洲对物质主义社会的幻想日益破灭,对精神的新欣赏也随之兴起。这种观念的转变常常通过对自然世界的重新评估来表达,因为弗里德里希、特纳和约翰·康斯特勃等艺术家试图将自然描绘成一种“与人类文明的诡计对立的神圣创造物”。
弗里德里希的作品在他早期的职业生涯中就为他带来了声誉,法国雕塑家大卫·丹格斯(David d'Angers)等同时代人都说他是一个发现了“景观悲剧”的人。然而,他的作品在晚年失宠,默默无闻地死去。随着德国在19世纪末走向现代化,一种新的紧迫感成为其艺术的特征,弗里德里希对静谧的沉思式描绘被视为过去时代的产物。20世纪初,他的作品再次受到人们的赞赏,从1906年开始,他在柏林举办了32幅画展。到了20世纪20年代,他的绘画被表现主义者发现,在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超现实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经常从他的作品中汲取灵感。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主义的兴起再次见证了弗里德里希受欢迎程度的回升,但随后他的画作由于与纳粹运动的联系而被解读为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因此其受欢迎程度急剧下降。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弗里德里希才重新获得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标志和国际重要画家的声誉。
生活
早年与家庭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于1774年9月5日出生于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瑞典波美拉尼亚格雷夫斯瓦尔德。他是十个孩子中的第六个,在父亲阿道夫·戈特利布·弗里德里希(Adolf Gottlieb Friedrich)的严格信条下长大,父亲是蜡烛制造者和肥皂制造者。家庭财务状况的记录相互矛盾;虽然一些消息来源表明这些孩子是在私人辅导下长大的,但另一些消息来源记录说,他们是在相对贫困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从小就熟悉死亡。他的母亲索菲于1781年去世,当时他七岁。一年后,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去世,另一个妹妹玛丽亚于1791年死于斑疹伤寒。可以说,他童年最大的悲剧发生在1787年,当时他的兄弟约翰·克里斯托夫去世:13岁时,卡斯帕·大卫目睹他的弟弟从结冰的湖面上摔下,溺水身亡。一些报道表明,约翰·克里斯托夫在试图营救卡斯帕·大卫时丧生,而卡斯帕·大卫也在冰上处于危险之中。
弗里德里希于1790开始了他的正式艺术研究,作为他在家乡格赖夫斯瓦尔德的的艺术家约翰·戈特弗里德·奎斯托普(Johann Gottfried Quistorp)的私人学生,艺术系现在被命名为卡斯帕戴维弗里德里希学院(Caspar-David-Friedrich-Institut)。奎斯托普带着他的学生们去户外画画;因此,弗里德里希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鼓励从生活中写生。通过奎斯托普,弗里德里希结识了神学家路德维希·戈特哈德·科塞加滕( Ludwig Gotthard Kosegarten),并受到其影响,他教导人们自然是上帝的启示。奎斯托普向弗里德里希介绍了17世纪德国艺术家亚当·埃尔斯海默的作品,他的作品通常包括以风景为主的宗教主题和夜间活动主题。在此期间,他还与瑞典教授托马斯·托里尔德(Thomas Thorild)一起学习文学和美学。四年后,弗里德里希进入享有盛名的哥本哈根学院,在那里,他开始接受教育,先复制古董雕塑的模型,然后开始从生活中绘画。住在哥本哈根使这位年轻的画家有机会接触到皇家美术馆收藏的17世纪荷兰风景画。在该学院,他在Christian August Lorentzen和风景画家Jens Juel等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这些艺术家的灵感来源于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运动,代表了新兴浪漫主义美学的戏剧性强度和表达方式与日渐衰落的新古典主义理想之间的中点。情绪是至高无上的,影响来自于诸如冰岛埃达传说( legend of Edda)、莪相(Ossian,爱尔兰英雄吟游诗人)和挪威神话中的诗歌等来源。
搬到德累斯顿
1798年,弗里德里希在德累斯顿永久定居。在这个早期阶段,他尝试版画制作,蚀刻版画和木刻版画的设计都是他哥哥做的。到1804年,他创作了18幅蚀刻画和四幅木刻画;它们显然是少量制作的,只分发给朋友。尽管他涉足其他媒体,但他还是倾向于主要使用墨水、水彩画和乌贼墨。除了一些早期作品,如《废墟中的寺庙风景》( Landscape with Temple in Ruins,1797年),他没有广泛从事油画创作,直到他的名声更加稳固。从1801年开始,他经常去波罗的海海岸、波希米亚、科诺什和哈尔茨山,这激发了他对风景的兴趣。他的绘画大多以德国北部的风景为基础,描绘了森林、山丘、港口、晨雾和其他基于对自然的密切观察的光线效果。这些作品以风景名胜的草图和研究为蓝本,如吕根悬崖、德累斯顿周边地区和易北河。他几乎完全用铅笔进行研究,甚至提供地形信息,但弗里德里希中期绘画中微妙的大气效果特征是凭记忆呈现的。这些效果的力量来自于对光线的描绘,以及太阳和月亮在云层和水面上的照明:波罗的海海岸特有的光学现象,以前从未如此强调过
1805年,他在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组织的魏玛竞赛中获奖,由此确立了他作为艺术家的声誉。当时,魏玛艺术大赛倾向于吸引平庸、现已被遗忘的艺术家,他们呈现出新古典主义和伪希腊风格的衍生混合。作品质量差开始损害歌德的声誉,因此当弗里德里展出两幅作品——《黎明游行》(Procession at Dawn)和《海边渔民》(Fisher-Folk by the Sea)时——诗人热情地回应并写道:“我们必须赞扬艺术家在这幅画中的足智多谋 相当。画得好,行进巧妙得体……他的处理结合了大量的坚定、勤奋和整洁……巧妙的水彩画……也值得称赞。”
弗里德里希在1808年34岁时完成了他的第一幅主要画作。《山中的十字架》是一幅祭坛画板,据说是为波希米亚杰钦(Tetschen)的一个家庭礼拜堂委托制作的。该画板描绘了山顶上的一个十字架,独自一人,四周是松树、 在基督教艺术中,祭坛画首次展示了一幅风景画。据艺术历史学家琳达·西格尔(Linda Siegel)说,弗里德里希的设计是“他早期许多描绘自然界十字架的绘画的逻辑高潮”。"
尽管祭坛画普遍受到冷遇,但这是弗里德里希的第一幅受到广泛宣传的画。艺术家的朋友们公开为这部作品辩护,而艺术评论家巴西利乌斯·冯·拉姆多尔(Basilius von Ramdohr)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质疑弗里德里希在宗教背景下对风景的运用。他拒绝了风景画可以传达明确含义的观点,写道“如果风景画潜入教堂并爬上祭坛,这将是一个真实的假设”。1809年,弗里德里希通过一个节目回应,描述了他的意图,将夕阳的光芒与圣父的光芒进行了比较。这一声明标志着弗里德里希唯一一次记录了对自己作品的详细解读,这幅画是弗里德里希收到的为数不多的委托之一。
在普鲁士王储购买了他的两幅画后,弗里德里希于1810年当选为柏林学院的成员。然而在1816年,他试图与普鲁士当局保持距离,并于6月申请撒克逊国籍。此举出乎意料,撒克逊政府是亲法的,而弗里德里希的画作普遍被视为爱国主义和明显的反法。尽管如此,在他在德累斯顿的朋友格拉夫·维茨敦·冯·埃克斯特(Graf Vitzthum von Eckstädt)的帮助下,弗里德里希获得了公民身份,并于1818年以每年150塔勒的红利成为撒克逊学院的成员。尽管他曾希望获得一个正式的教授职位,但根据德国信息图书馆(German Library of Information)的说法,这一职位从未授予他,因为“人们认为他的绘画过于个人化,他的观点过于个人化,无法成为学生们富有成效的榜样。”政治也可能是阻碍其职业生涯的一个因素:弗里德里希的明显的日耳曼主题和消费经常与当时盛行的亲法态度发生冲突。
结婚
1818年1月21日,弗里德里希与卡罗琳·波默(Caroline Bommer)结婚,卡罗琳·波默是一位来自德累斯顿的染工的25岁女儿。这对夫妇有三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艾玛是1820年出生的。生理学家兼画家卡尔·古斯塔夫·卡鲁斯(Carl Gustav Carus)在他的传记文章中指出,婚姻对弗里德里希的生活或性格都没有重大影响,但他这一时期的油画,包括蜜月后的《吕根岛上的白垩岩》,显示出一种新的轻浮感,而他的调色板则更明亮、更不严肃。在这一时期的绘画中,人物的出现越来越频繁,西格尔将其解释为“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尤其是他的家庭,现在越来越多地占据了他的思想,他的朋友、他的妻子和他的市民成为他艺术中经常出现的主题。”
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在俄罗斯找到了两个来源的支持。1820年,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大公( Grand Duke Nikolai Pavlovich)应其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Alexandra Feodorovna)的要求,参观了弗里德里希的画室,并带回了他的一些画作,这一交换开始了持续多年的赞助。此后不久,亚历山大二世的导师、诗人瓦西里·朱可夫斯基(Vasily Zhukovsky)于1821年与弗里德里希(Friedrich)相遇,并在弗里德里希身上找到了志趣相投的人。几十年来,朱可夫斯基通过亲自购买弗里德里希的作品和向王室推荐他的艺术作品来帮助弗里德里希。在弗里德里希职业生涯结束时,他的帮助对这位身患重病、一贫如洗的艺术家来说是无价的。朱可夫斯基说,他朋友的画“精确地取悦了我们,每一幅都唤起了我们心中的记忆。”
弗里德里希认识Philipp Otto Runge,他是浪漫主义时期另一位德国著名画家。他也是Georg Friedrich Kersting和挪威画家约翰·克里斯蒂安·达尔的朋友,在朴素的画室里为他作画。达尔在艺术家的最后几年与弗里德里希关系密切,他对购买艺术品的公众感到沮丧,因为弗里德里希的画只是“珍品”。诗人朱可夫斯基欣赏弗里德里希的心理主题,达尔赞扬弗里德里希风景画的描述性,并评论说“艺术家和鉴赏家在弗里德里希的艺术中只看到了一种神秘主义,因为他们自己只是在寻找神秘主义者……他们没有看到弗里德里希在他所代表的一切事物中忠实而认真地研究自然”。
在此期间,弗里德里希经常为陵墓绘制纪念性纪念碑和雕塑,反映出他对死亡和来世的痴迷;他甚至还为德累斯顿公墓中的一些葬礼艺术设计。其中一些作品在烧毁慕尼黑玻璃宫(Glass Palace,1931年)的大火中丢失,后来在1945年德累斯顿爆炸案中丢失。
晚年与死亡
在弗里德里希生命的最后15年里,他的声誉稳步下降。随着早期浪漫主义的理想从时尚中消失,他逐渐被视为一个古怪而忧郁的人物,与时代脱节。他的赞助人渐渐地消失了。到1820年,他已经过着隐士的生活,朋友们称他为“孤独中最孤独的人”。他临终时生活相对贫困。他变得孤立无援,日夜长时间独自在树林和田野里散步,常常在日出前开始散步。
1835年6月,弗里德里希第一次中风,导致他四肢瘫痪,大大降低了他的绘画能力。因此,他无法进行油画工作;取而代之的是,他仅限于水彩画、乌贼墨画和对旧作品的重新创作。
虽然他的视力仍然很强,但他已经失去了手的全部力量。然而,他最终创作了一幅《月光下的海岸》,被沃恩(Vaughan)描述为“他所有海岸线中最黑暗的一幅,其中丰富的色调弥补了他以前技巧的不足”。
死亡的象征出现在他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中。在他中风后不久,俄罗斯皇室购买了他早期的一些作品,这些收益使他得以前往今天捷克共和国的泰普利茨( Teplitz)恢复健康。
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弗里德里希开始了一系列的肖像画,他又回到了观察大自然中的自己。然而,正如艺术史学家威廉·沃恩(William Vaughan)所观察到的那样,“他可以将自己视为一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人。他不再是1819年《凝月(新大师画廊藏)》中出现的那种正直、支持的人物。他又老又僵硬……他弯腰走路。”。
到1838年,他只能绘制小规模作品。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越来越依赖朋友的帮助慈善。
弗里德里希于1840年5月7日在德累斯顿去世,葬在市中心以东的德累斯顿三一公墓(Trinitatis-Friedhof,Trinity Cemetery,大约15年前他曾画过的入口)。这座简朴平坦的墓碑位于主大道内中央圆形建筑的西北方向。
到他去世时,他的声誉和名望都在下降,他的去世在艺术界几乎没有引起注意。他的作品在他有生之年肯定得到了认可,但并不广泛。虽然在当代艺术中,对风景的仔细研究和对自然精神要素的强调是司空见惯的,但他的作品过于独创和个人化,难以被充分理解。到1838年,他的作品不再畅销,也不再受到评论家的关注,浪漫主义运动已经远离了艺术家帮助建立的早期理想主义。
卡尔·古斯塔夫·卡鲁斯在他死后写了一系列文章,赞扬弗里德里希对风景画传统的转变。然而,卡鲁斯的文章坚定地将弗里德里希置于他那个时代,并没有将这位艺术家置于一个持续的传统之中。他的画作中只有一幅被复制成印刷品,而且复制品很少。
主题
景观与崇高
新的风景画家在自然界中看到的100度的视野,他们无情地挤在一起,形成一个只有45度的视角。此外,自然界中被大空间隔开的东西,被压缩成一个狭窄的空间,使眼睛过度充盈和满足,对观看者造成不利和令人不安的影响。
—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
以全新的方式对景观进行可视化和描绘是弗里德里希的关键创新。他不仅像经典观念中那样探索美丽景色的极乐享受,而且还通过对自然的沉思来审视崇高的瞬间,与精神自我的重聚。弗里德里希有助于将艺术中的风景从人类戏剧的背景转变为独立的情感主题。弗里德里希的画作通常使用背后视角( Rückenfigur)——一个从背后观察风景的人。观众被鼓励将自己置于人物后端的位置,通过这种方式,他体验到大自然的崇高潜力,理解到场景是由人类感知和理想化的。弗里德里希创造了一个充满浪漫情怀的景观概念。他的艺术描绘了广泛的地理特征,如岩石海岸、森林和山景。他经常用风景来表达宗教主题。在他那个时代,大多数最著名的绘画都被视为宗教神秘主义的表现。
弗里德里希说:“艺术家不仅应该画他眼前看到的东西,还应该画他内心看到的东西。但是,如果他什么也看不到,那么他也应该避免画他眼前看到的东西。否则,他的画将像那些折叠式屏风,人们期望在它后面只能看到病人或死者。”广阔的天空、风暴、薄雾、森林、废墟和十字架见证了上帝的存在,这些都是弗里德里希风景中常见的元素。虽然死亡在远离海岸的船只上有象征性的表达——一种像卡戎(Charon)一样的图案,在白杨树上也有,但在《橡树下的寺院》等画作中,死亡更直接地被提及。在这些画作中,僧侣们抬着棺材穿过一座敞开的坟墓,走向十字架,穿过一座废墟教堂的大门。
他是第一批描绘冬季风景的艺术家之一,在这些风景中,土地被渲染成了死气沉沉的样子。弗里德里希的冬季场景是庄严的,根据艺术历史学家赫尔曼·比恩肯(Hermann Beenken)的说法,弗里德里希画的冬季场景中“还没有人站稳脚跟。几乎所有较老的冬季图片的主题都不是冬天本身,而是冬天的生活。在16和17世纪,人们认为不可能忽略诸如滑冰者人群、流浪者……正是弗里德里希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然生命的完全超然和独特的特征。他寻找的不是许多音调,而是一种音调;因此,在他的风景画中,他把合成和弦放在一个单一的基本音符中”。
光秃秃的橡树和树桩,如《乌鸦树》、《凝月(国家美术馆藏)》和《夕阳下的柳树丛》(Willow Bush under a Setting Sun ),是弗里德里希绘画中反复出现的元素,象征着死亡。与绝望相对应的是弗里德里希救赎的象征:十字架和晴朗的天空预示着永生,细长的月亮暗示着希望和基督越来越亲近。在他的海洋绘画中,锚经常出现在岸边,也表明了一种爱精神上的希望。德国文学学者艾丽斯·库兹尼亚尔(Alice Kuzniar)在弗里德里希的绘画中发现了一种时间性,一种在视觉艺术中很少被强调的对时间流逝的唤起。例如,在奥克伍德的修道院,僧侣们离开敞开的坟墓,走向十字架和地平线的运动传递了弗里德里希的信息,即人类生命的最终目的地在坟墓之外。
黎明和黄昏构成了他风景画的突出主题,弗里德里希晚年的特点是日益悲观。他的作品变得更加黑暗,显示出一种可怕的纪念性。《冰之海》——也许是对弗里德里希在这一点上的思想和目标的最好概括,尽管以一种激进的方式,这幅画并不受欢迎。它完成于1824年,描绘了一个严峻的主题,北冰洋的一次海难。“他制作的图像,用石灰华颜色的浮冰磨碎了一艘木船,超越了纪录片,变成了寓言:人类渴望的脆弱树皮被世界巨大的冰川冷漠所粉碎。”
弗里德里希对美学的书面评论仅限于1830年制定的一套格言,其中他解释了艺术家需要将自然观察与对自己个性的内省审视相匹配。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建议艺术家“闭上你的肉体之眼,这样你就可以先用精神之眼看到你的画,然后把你在黑暗中看到的东西带到白昼的光中,这样它就可以从外面到里面对别人作出反应。”他拒绝在“整体性”中过度描绘自然,正如Ludwig Richter和约瑟夫·安东·科赫等当代画家的作品中所发现的那样。
孤独与死亡
弗里德里希的生活和艺术有时被一些人认为带有一种压倒性的孤独感。艺术史学家和一些与他同时代的人将这种解释归因于他年轻时所遭受的损失,归因于他成年后的暗淡前景,而弗里德里希苍白而孤僻的外表有助于强化“来自北方的沉默寡言的人”的流行观念。
弗里德里希在1799年、1803年至1805年、约1813年、1816年以及1824年至1826年间经历了抑郁发作。在这些插曲中,他创作的作品出现了明显的主题变化,出现了秃鹫、猫头鹰、墓地和废墟等主题和符号。从1826年起,这些图案成为他作品的永久特征,而他对颜色的使用变得更加黑暗和柔和。卡鲁斯在1929年写道,弗里德里希“被精神上的不确定性所笼罩”,尽管著名艺术史学家和策展人休伯特斯·加斯纳(Hubertus Gassner)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弗里德里希的作品中有一种积极的、肯定生命的潜台词,其灵感来自共济会和宗教。
日耳曼民俗
1813年法国占领波美拉尼亚期间,弗里德里希的爱国主义和怨恨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来自德国民间传说的主题越来越突出。弗里德里希是一位反法的德国民族主义者,他用自己家乡的风景画来庆祝日耳曼文化、习俗和神话。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和西奥多·科尔纳(Theodor Körner)的反拿破仑诗歌以及亚当·穆勒(Adam Müller)和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爱国主义文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弗里德里希被三位朋友在与法国的战争中丧生以及克莱斯特(Kleist)1808年的戏剧《赫尔曼战役》(Die Hermannsschlacht)所感动,他创作了一系列绘画作品,试图仅通过风景来传达政治象征——这在艺术史上尚属首次。
在《为独立而战的阵亡将士陵墓》中,一座刻有“阿米纽斯”(Arminius)字样的破旧纪念碑唤起了民族主义的象征——日耳曼酋长,而四座倒下英雄的陵墓略微半开着,让他们的灵魂永远自由。两名法国士兵以小人物的身份出现在一个洞穴前,洞穴较低且较深,四周环绕着岩石,似乎离天堂更远。第二幅政治画作《森林中的猎人》描绘了一位迷路的法国士兵,被茂密的森林衬托得矮小,而树桩上栖息着一只乌鸦——一位末日预言家,象征着法国的预期失败。
遗产
影响
与其他浪漫主义画家一起,弗里德里希帮助将风景画定位为西方艺术的主要流派。在他的同时代人中,弗里德里希的风格对约翰·克里斯蒂安·达尔的绘画影响最大。在后来的几代人中,阿诺德·伯克林深受其作品的影响,而弗里德里希的作品大量出现在俄罗斯收藏品中影响了许多俄罗斯画家,特别是阿基普·奎因芝和伊万·希什金。弗里德里希的精神期待着美国画家,如艾伯特·平克汉姆·莱德、拉尔夫·阿尔伯特·布莱克洛克、哈德逊河学派和新英格兰发光派画家。
20世纪之交,挪威艺术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奥伯特( Andreas Aubert ,1851-1913)重新发现了弗里德里希,他的作品开创了现代弗里德里希学术,象征主义画家也重新发现了弗里德里希,他们珍视他的幻想和寓言风景。挪威象征主义者爱德华·蒙克在19世纪80年代访问柏林时可能会看到弗里德里希的作品。蒙克1899年的印刷品《两个人,孤独的人》与弗里德里希的《云海之上的徒步者》相呼应,尽管在芒克的作品中,重点已经从广阔的风景转向前景中两个忧郁人物之间的错位感。
弗里德里希的现代复兴在1906年获得了动力,当时他的32幅作品在柏林的浪漫主义时期艺术展上展出。他的风景画对德国艺术家马克斯·恩斯特的作品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其他超现实主义者开始将弗里德里希视为他们运动的先驱。1934年,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在他的作品《人类状况》中表达了敬意,这部作品直接呼应了弗里德里希艺术中对感知和观众角色的质疑。几年后,超现实主义杂志《米诺陶》(Minotaure)在1939年由评论家玛丽·兰茨伯格(Marie Landsberger)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弗里德里希,从而将他的作品展示给了更广泛的艺术家圈。恩斯特的狂热崇拜者保罗·纳什在1940-1941年间的作品《死海》中,就可以明显看出《冰之海》的影响。弗里德里希的作品被其他20世纪的主要艺术家引用为灵感来源,包括马克·罗斯科、格哈德·里希特、哥达德·格拉布纳(Gotthard Graubner)和安塞姆·基弗。弗里德里希的浪漫主义绘画也被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89)挑了出来,他站在《凝月(国家美术馆藏)》面前说:“你知道,这是《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的源泉。”
艺术史学家罗伯特·罗森布鲁姆(Robert Rosenblum)在其1961年发表的文章《抽象崇高》(The Abstract Sublime)中,将弗里德里希和特纳的浪漫主义风景画与马克·罗斯科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进行了比较。罗森布卢姆特别描述了弗里德里希1809年的《海边的僧侣》、特纳的《夜星》(The Evening Star)和罗斯科1954年的《光、大地和蓝色》(Light, Earth and Blue),这些作品揭示了视觉和情感的密切关系。据罗森布鲁姆说,罗斯科,像弗里德里希和特纳一样,把我们置于崇高美学家所讨论的那些无形的无限的门槛上。弗里德里希作品中的和尚和特纳作品中的费舍尔在泛神论上帝的无限浩瀚和他的生物的无限渺小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罗斯科的抽象语言中,这样的文字细节——真正的观众和先验景观呈现之间的移情桥梁——已不再必要。我们自己就是海前的和尚,静静地、沉思地站在这些巨大而无声的画面前,仿佛我们在看日落或月夜。"
当代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普尔(Christiane Pooley)从弗里德里希(Friedrich)的作品中获得灵感,她的风景画重新诠释了智利的历史。
批评意见
直到1890年,尤其是在他的朋友去世后,弗里德里希的作品几乎被遗忘了几十年。然而,到了1890年,他的作品中的象征意义开始与当时的艺术氛围相吻合,尤其是在中欧。然而,尽管人们对他的独创性重新产生了兴趣,并承认了他的独创性,但他对“绘画效果”的缺乏关注而且渲染得很薄的表面与当时的理论格格不入。
当时代的要求与我的信念背道而驰时,我不会软弱到屈服于时代的要求。我在自己周围织了一个茧,让其他人也这样做。我将把它留给时间来展示它将带来什么:一只灿烂的蝴蝶或蛆。
—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
20世纪30年代,弗里德里希的作品被用于宣传纳粹意识形态,试图将这位浪漫主义艺术家融入民族主义的血与土(Blut und Boden)。弗里德里希的声誉花了几十年才从与纳粹主义的联系中恢复过来。他对象征主义的依赖以及他的作品不属于现代主义狭义定义的事实导致了他的失宠。1949年,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写道,弗里德里希“以他那个时代的冰冷技术工作,这很难激发现代绘画流派的灵感”,并暗示艺术家试图在绘画中表达最好留给诗歌的东西。克拉克对弗里德里希的辞退反映了这位艺术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声誉受到的损害。
弗里德里希的形象被一些好莱坞导演采用,比如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这进一步损害了弗里德里希的声誉。他的形象是建立在弗里茨·朗(Fritz Lang)和F.W.穆诺(Friedrich Wilhelm Murnau)等德国电影大师的恐怖和幻想类型作品的基础上的。他声誉的康复是缓慢的,但通过沃纳·霍夫曼(Werner Hofmann)、赫尔穆特·贝尔什·苏潘(Helmut Börsch-Supan)和西格丽德·辛茨(Sigrid Hinz)等批评家和学者的著作,他的恢复得到了加强,他们成功地拒绝和反驳了归因于他的作品的政治联想,并将其置于纯粹的艺术历史背景中。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再次在世界各地的主要画廊展出,因为他受到了新一代评论家和艺术史学家的青睐。
今天,他的国际声誉已经确立。他是祖国德国的民族偶像,受到西方世界艺术史学家和艺术鉴赏家的高度评价。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心理复杂的人物,沃恩认为,一个与怀疑作斗争的信徒,一个被黑暗困扰的美丽的庆祝者。最终,他超越了诠释,通过其形象的引人注目的吸引力跨越了文化。他真的变成了一只蝴蝶,希望它永远不会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
作品
弗里德里希是一位多产的艺术家,创作了500多件作品。与他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理想相一致,他打算让他的绘画成为纯粹的审美陈述,因此他谨慎地认为,他的作品的标题不太具有描述性或唤起性。很可能,今天一些更具文字色彩的标题,如《生命阶段》,并非由艺术家本人给出,而是在弗里德里希的一次兴趣复兴中采用的。约会弗里德里希的作品时会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部分原因是他经常不直接给自己的画布命名或注明日期。然而,他在自己的作品上保留了一个详细的笔记本,学者们用它来将绘画与完成日期联系起来。
卡斯帕·弗里德里希作品收藏于:
Museum Behnhaus Drägerhaus - Lubecker Museen(2)
Museum fur Kunst und Kulturgeshichte der Hanestadtd Lubeck(2)
Thüringer Landesmuseum Heidecksburg(1)
Kupferstichkabinett - Dresden(1)
Museum Gunzenhauser - Kunstsammlungen Chemnitz(1)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Museum of Art(1)